作者=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Sandel)
文源=「公正:何谓正当之为」摘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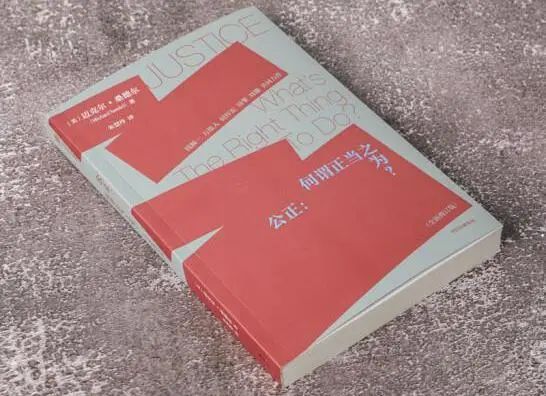
━ ━ ━
–为钱怀孕–
威廉·斯特恩和伊丽莎白·斯特恩夫妇住在新泽西州特纳夫莱市。丈夫是一位生物化学家,妻子是一名儿科医生。他们想要一个孩子,可是无法自己生育,至少生育会给伊丽莎白带来生命危险——她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因此,他们联系了一家安排“代孕”的不孕不育中心,该中心刊登广告以寻求“代孕母亲”——愿意为他人怀孕分娩,并以此获得报酬的妇女。
应征者中有一个女子名叫玛丽·贝丝·怀特海,29岁,有两个孩子,是一名环卫工人的妻子。1985年2月,威廉·斯特恩和玛丽·贝丝·怀特海签订了一份合同。玛丽同意用威廉的精子进行人工授精,然后生下孩子,并将其交给威廉。她还同意放弃她的母亲权利,这样伊丽莎白·斯特恩就可以收养这个孩子。就威廉这一方而言,他愿意支付玛丽1万美元(分娩时支付),外加医疗开支。(他还向该不孕不育中心支付了7 500美元,因为后者为他们安排了这次交易。)
经过多次人工授精,玛丽·贝丝·怀特海怀孕了,并于1986年3月产下一名女婴。斯特恩夫妇盼望马上就能领养他们的女儿,给她起名为梅丽莎。然而,玛丽·贝丝·怀特海却改变了主意,她不想交出孩子,于是带着孩子逃到了佛罗里达。但是斯特恩夫妇获得了法院命令,要求她交出孩子。佛罗里达警方找到玛丽,把这个孩子交给了斯特恩夫妇,而接下来关于监护权的争夺战也在新泽西的法院展开。
初审法官不得不决定是否应该执行这份合同。你认为应当如何判决?为了使事情简化,让我们集中研究相关的道德问题,而不是法律。(事实上,新泽西当时并没有允许或禁止代孕合同的法律。)威廉·斯特恩和玛丽·贝丝·怀特海签署了一份合同,从道德上来看,它是否应当得到执行呢?
赞成执行该合同的最强有力的论点就是:交易就是交易。两个法定的成年人自愿达成了一个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协议:威廉·斯特恩将得到一个跟他有基因关联的孩子,玛丽·贝丝·怀特海将会因为9个月的工作而获得1万美元。
不可否认,这不是一桩普通的商业交易。因此,你可能会基于以下两个理由中的一个,犹豫是否要执行这份合同。首先,你可能会怀疑,当一个女人在同意为了钱而生孩子并在生下来之后放弃他的时候,她是否完整地得到了信息。她是否真的能预料到,当她要放弃这个孩子时,她会是什么感觉?如果不能,那么人们可能认为,她最初的同意被对金钱的需求蒙蔽,也由于不够了解与孩子分开会怎样而被蒙蔽。其次,你可能会发现买卖孩子或租赁妇女的生育能力是不对的,即使双方都自由地同意这样做。人们可能会争辩道,这一行为将孩子变成了商品,并通过将怀孕和生孩子看成赚钱的交易而剥削利用了妇女。
正如后来众所周知的那样,“婴儿M”这一案件的初审法官哈维·索尔考并没有被这些反驳中的任何一个说服。他援引合同的不可侵犯性来维护这一协议。交易就是交易,这名生育母亲并不能仅仅因为自己改变了主意就有权利解除合约。
该法官讨论了上述两种反驳。首先,他反对这样一种看法——玛丽·贝丝的同意并不是自愿的,她的同意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问题的:
没有任何一方占据更高的交易地位。每一方都拥有对方想要的东西。每一方的服务价格都已经确定,因此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没有一方强迫另一方,没有一方拥有专门知识而让另一方处于不利地位,也没有一方拥有不相称的交易权力。
其次,他反驳了这样一种看法——代孕等同于出卖婴儿。索尔考法官认为,威廉·斯特恩是孩子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他并没有从玛丽·贝丝·怀特海那里购买婴儿。他只是因为她提供了怀孕和分娩的这一服务,而给她支付了报酬。“出生后,这位父亲并没有购买这个孩子,她是与他自己的生物基因有关联的孩子。他不能购买已经属于他的东西。”由于这个孩子是威廉的精子致孕而来,那么她从一开始就是他的孩子。因此,这里并没有涉及出售婴儿。那1万美元的报酬是为一项服务(怀孕)而非一个产品(这个孩子)支付的。
对于那种认为提供这样的服务剥削利用了妇女的观点,索尔考法官也提出了异议。他比较了有偿怀孕和有偿精子捐献。既然男人可以出售他们的精子,那么女人就应当能够出售她们的生育能力:“如果一个男人可以提供生育的手段,人们就必须同等地允许女人也这样做。”他陈述道,与此相反的主张才是否定女人同等地受到法律保护。
玛丽·贝丝·怀特海将这一案件上诉至新泽西最高法院。该法院全体一致推翻了索尔考法官的判决,判定这一代孕合同无效。然而,它将梅丽莎的监护权判给了威廉·斯特恩,理由是:这对孩子来说最好。法官将合同搁置一旁,认为斯特恩夫妇会更好地养育梅丽莎,然而,他们恢复了玛丽·贝丝·怀特海作为孩子母亲的身份,并要求低级法院给予她探视权。
在为法庭写结案陈词时,首席大法官罗伯特·威伦茨反驳了代孕合同。他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自愿的合同,而且它包含了买卖婴儿的成分。
第一个理由是,这里的同意是有缺陷的。玛丽·贝丝·怀特海在同意生养一个孩子并在出生后将孩子返还他人时,并不是真正自愿的,因为她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信息:
在这一合同中,那位自然意义上的母亲在了解她与孩子之间那种纽带的力量之前,给出了不可撤销的承诺。她从来都没有做出一个完全自愿的、基于完整信息的决定。因为很明显,任何在孩子出生之前所做出的决定,在其最重要的意义上,都是信息不全面的。
一旦这个孩子出生了,这个母亲就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来做出一个信息全面的决定。可是到那时,她的决定就不自由了,而是被“起诉的威胁及1万美元报酬的诱惑”强迫,这使得这个决定“并不完全是自愿的”。此外,对金钱的需要,使得这个贫困的女子很可能会“选择”去给富人当代孕母亲,而不是“被选择”。威伦茨法官提议说,这一点也质疑了这类协议所具有的自愿特征:“我们怀疑,低收入阶层的不孕不育夫妇,是否会找高收入的人代孕。”
因此,使得这份合同无效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里的同意是有问题的。然而,威伦茨法官还提出了第二个更具根本性的理由:
先将她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金钱需要的强迫,以及她对最终结果的理解有多深入这些问题搁置一边,我们认为她的同意是无关紧要的。在一个文明的社会,有一些东西是金钱不能购买的。
威伦茨认为,商业性的代孕等同于出售婴儿,而出售婴儿是不对的,无论这是否出于自愿。他反驳了这一观点——这里的报酬是为了代孕母亲的服务,而非为了这个孩子。根据这份合同,只有当玛丽·贝丝交出监护权并终止其做母亲的权利时,才能向她支付这1万美元。
这就是在出售一个孩子,至少是在出卖一个母亲对其孩子所拥有的权利。这里唯一缓和的因素在于,购买者是孩子的父亲……一个中间人受利益驱动而促成了这桩买卖。无论是什么样的理想推动了任何一方,利益的动机都支配、渗入并最终控制了这一交易。
–代孕合同与正义–
那么,在“婴儿M”一案中,到底谁是对的呢?是执行该合同的初级法院,还是废除该合同的高级法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评估合同所具有的道德力量,以及在反对代孕合同时所提出来的两种反驳。
那种支持代孕合同的论点所依据的是我们迄今所考察的两种正义理论——自由至上主义和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者支持合同的理由是,它们反映了选择的自由。支持两个相互同意的成年人之间所达成的合同,就是尊重他们的自由。功利主义者支持合同的理由是,它们推进了总体福利。如果双方都认同一桩交易,那么双方都肯定能从这一协议中获得一些利益或幸福,否则他们就不会做这笔交易。因此,除非我们能够证明这一交易减少了另外一些人的功利(而且要超过它给交易双方所带来的利益),否则,那些双方获利的交换(包括代孕合同)就应当得到支持。
这些反驳有道理吗?它们具有多少说服力呢?
▣反驳1:有问题的同意
第一种反驳——关于玛丽·贝丝·怀特海的同意是否真正地出于自愿——引发了一个与条件有关的问题,即人们在哪些条件下做出选择。它认为只有当我们并没有被过分地压迫(如对金钱的需要),并合理且完整地掌握了备选项的信息时,我们才能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利。当然,关于什么算作过分的压力,什么算作缺乏信息的同意,人们还会有争论。可是,这种争论的要点在于判断什么时候一份看上去像自愿的协议是真正自愿的,什么时候不是。这一问题清楚地体现于“婴儿M”一案中,正如它体现于关于志愿兵役制的争论中一样。
如果我们从这些案例中退后一步,那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关于一个有意义的许诺的必要背景条件的争论,实际上是我们在本书中所考察的三种考量正义的进路之一(认为正义就意味着尊重自由)的家族内部的争论。正如我们所见,自由至上主义就是这个家族中的一员,它认为,正义需要尊重人们所做出的任何选择,假如这些选择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其他一些将正义看作尊重自由的理论家则在选择的条件上设定了一些限制。他们认为——正如法官威伦茨在“婴儿M”一案中所说的那样——迫于压力或信息掌握不全面的许诺,并不是真正地出于自愿。当我们开始讨论约翰·罗尔斯(一个自由阵营内部的成员,反对自由至上主义关于正义的论述)的政治哲学时,我们将会更有能力来评价这一争论。
▣反驳2:贬低与更高的善
那么,对代孕合同的第二种反驳——认为有些东西是我们不应当用金钱购买的,包括婴儿和妇女的生育能力的观点——又如何呢?买卖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错呢?对此,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就是:将婴儿和怀孕看作商品就是贬低了他们,而没有适当地尊重他们。
潜藏在这种答案背后的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思想:正确地尊重商品和社会行为的方式,并不仅仅取决于我们。特定的尊重模式适用于特定的商品和行为。关于商品,如汽车和烤面包机,最合适的尊重它们的方式就是使用它们,或制造、出售它们以获得利益。可是,如果我们将所有的事物都看作商品,那就错了。例如,将人类看作商品——看作可以买卖的物品,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人类是值得尊重的而不是被使用的对象。尊重和使用是两种不同的重视模式。
当代道德哲学家伊丽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便将这种论点运用于关于代孕的争论。她认为,代孕合同由于将孩子和妇女的劳动看作商品,因而贬低了他们。这里她所说的“贬低”,意指“根据一种较低的而非适合某物的评价模式来对待它。我们不是‘更多’或‘更少’地评价事物,而是以质量更高或更低的方式对待事物。爱一个人或尊重一个人,就是以一种高于这个人被利用时所受的对待方式对待他……商业化的代孕贬低了孩子,因为它将孩子看作商品。”它将他们作为赚钱的工具加以利用,而不是把他们当作值得爱护和关心的人加以珍惜。
安德森认为,商业化的代孕将妇女的身体看作工厂,并付钱让她们与自己所生的孩子脱离关系,从而贬低了妇女。它用那些管理普通生产的各种经济规范,代替了“通常管理孕育孩子的亲子规则”。安德森写道,通过要求代孕母亲“压抑她对这个孩子产生的母爱”,代孕合同“将妇女的劳动转换成一种异化了的劳动”。
在代孕合同中,(母亲)同意不与她的后代形成或试图形成一种母子关系。她的劳动是异化了的,因为她必须放弃其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怀孕这一社会行为所正当地促进的——一种与她的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
安德森的中心论点是:物品之间有所差别,因此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所有的物品——将其作为赚钱的工具或被利用的对象——是不对的。如果这一观点是对的,那么它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东西是金钱不能购买的。
这一论点也对功利主义发起了挑战。如果正义仅仅是使快乐减去痛苦后的余额最大化,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单一的、整齐划一的方式,来衡量和评价所有的事物及其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或痛苦。边沁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提出了功利的概念。可是安德森认为根据功利来评价所有的事物,就贬低了那些更适合用更高的规范来加以评价的各种事物和社会行为——包括孩子、怀孕和对子女的养育。
可是,这种更高的规范是什么呢?我们又怎么能知道哪些评价模式适合于哪些物品和社会行为呢?这一问题的解决路径之一开始于自由的观念。人类拥有实现自由的能力,因此我们不应当仅仅被当作对象而加以利用,相反,我们应当得到体面而尊敬的对待。这种解决的路径强调(值得尊敬的)人与(仅供使用的)对象或物品之间的区别,是道德中最具根本性的区别。对这一路径的最伟大的辩护者就是伊曼努尔·康德,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他。
对更高规范的另一种讨论路径始于这样一种观念:评价事物和社会行为的正当方式取决于这些行为所满足的目的。让我们回想一下,在反对代孕的时候,安德森论述道,“怀孕这一社会行为正当地促进了”一种特定的目的,即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一份要求这个母亲不要形成这样一种纽带的合同是带有贬低性的,因为这使她远离了这一目的。它以一种“商业生产的规范”代替了“亲子关系的规范”。这种思想——我们试图抓住这些行为的本质性目的或意图,以此来鉴别出适合这些社会行为的各种规范——正是亚里士多德正义理论的核心。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考察他的论证过程。
我们只有考察了这些道德和正义理论,才能真正地确定哪些物品和社会行为应当由市场管制。然而,关于代孕的争论如同关于志愿兵役制的争论一样,让我们瞥见了那危如累卵的一面。
–怀孕外包–
曾经作为“婴儿M”而广为人知的梅丽莎·斯特恩从乔治·华盛顿大学宗教学专业毕业了。此时距离新泽西的那场著名的关于她的监护权的争夺已经有二十余载,可是关于代孕母亲的争论仍然在继续。欧洲许多国家禁止商业性代孕;在美国,超过12个州使这一行为合法化了,另有12个州禁止这一行为,而在其他一些州,代孕合法与否仍然不是很明确。
新的生育技术在很多方面改变了代孕经济,并加深了它所体现的伦理困境。当玛丽·贝丝·怀特海同意为了报酬而怀孕时,她提供了卵子和子宫,因此她是婴儿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然而,试管授精的出现使得由一位妇女提供卵子而由另一位来孕育受精卵成为可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商业管理教授德博拉·斯帕(Deborah Spar)分析了这种新型代孕的商业优势。从传统意义上来说,那些签署代孕合同的人“本质上是要购买一个‘卵子加子宫’的包裹”,现在他们可以“从一处获得卵子(多数情况下包括那个有意向的母亲),而从另一处获得子宫”。
斯帕解释道,这种供应链条的断开,推动了代孕市场的发展。“通过断开卵子、子宫和母亲这条传统的连接,妊娠代理减少了那些围绕着传统代孕的法律上和情感上的危险,并因此给一个新型市场的繁荣打开了空间。”“由于从卵子——子宫这一捆绑中解脱出来”,代孕代理人如今在选择代孕者时“更加具有歧视性”——“寻找带有特殊基因特征的卵子,以及依附于某种特定人格的子宫”。那些可能要代孕的父母,不再需要担心被他们雇用来孕育他们的孩子的那个女子的基因特征,“因为他们从别处获得了这些”。
他们不在乎她长得怎么样,也不再那么担心她在生出孩子后会索要孩子,或法庭将倾向于帮助她。他们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健康的妇女,愿意经受怀孕的辛苦以及在怀孕期间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不喝酒,不抽烟,不吸毒。
尽管妊娠代理增加了预期代孕者的供应量,但需求量同样有所增加。如今,代孕者每次怀孕可以得到2万~2.5万美元的报酬。一次这样的安排(包括医疗费用和法律费用)一般来说总共要花费7.5万~8万美元。
由于价格飙升,人们不难发现那些准备找人代孕的夫妻开始寻找便宜一些的替代者。像在全球经济中的其他商品和服务一样,有偿怀孕开始被承包给廉价的供应方。2002年,印度将商业性代孕合法化,以期望吸引国外的顾客。
位于印度西部的小镇阿嫩德很快将成为有偿代孕中心,就像班加罗尔是呼叫中心一样。2008年,这个城市有超过50名妇女为来自美国、英国及其他地方的夫妇代孕。那里有一家诊所,给15个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当代孕母亲的孕妇提供集体住房,并配有仆人、厨师和医生。这些妇女所赚的钱从4 500美元到7 500美元不等,通常超过她们15年所赚的钱,并使她们能够购买一栋房子或支付她们自己孩子的教育费用。对那些满怀希望奔赴阿嫩德的夫妇而言,这一安排是一桩好买卖,总开支大约为2.5万美元(包括医疗支出、代孕者的报酬、往返机票、两次旅程的旅馆开销),大概是在美国代孕总开销的1/3。
有些人认为当代所实施的这些商业性代孕与那份引发“婴儿M”案件的合同相比,在道德上不是那么令人困惑了。这种观点认为,由于代孕者并不提供卵子,而只是提供子宫和怀孕的劳动力,因此这个孩子在基因上并不是她的。根据这种观点,这里没有出售孩子的说法,对孩子的索要也不太可能会遭到代孕者的反对。
可是怀孕外包并没有解决这一道德困境。代孕者跟她们所生的孩子之间,也许真的不像提供卵子的代孕者与她们所生的孩子之间联系得那样紧密。然而,将母亲这一角色划分成三种(养母、提供卵子者、代孕者)而非两种,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谁更有权利索要这个孩子?
如果说因试管授精而产生的怀孕外包带来了什么,那就是它使得这些道德问题进一步放大。想要找人代孕的夫妇省下来的代孕费用,以及印度代孕母亲从这一行为中所获得的与当地工资收入相差巨大的经济收益,让我们不可否认商业性的代孕可以增加整体福利。因此,从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很难反对这种作为全球化产业的有偿怀孕。
然而,这种全球化的怀孕外包同样也凸显了相关的道德困境。26岁的印度妇女苏曼·多蒂娅曾是一对英国夫妇的代孕者,在此之前,她是一个女仆,每个月的收入是25美元。工作9个月就能挣4 500美元对她来说具有太强大的吸引力,以至于让她无法拒绝。她在家里生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并且从来没有看过医生的事实,增加了她作为代孕母亲的心酸。当谈到她的有偿怀孕时,她说:“我现在比我怀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还要小心。”尽管成为一个代孕母亲给她带来的经济收益是非常显著的,可是,我们却不能断定这个选择是自由的。此外,一个有偿怀孕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形成——在贫困国家受到目的明确的政策的驱使——反映了代孕将妇女的身体和生育能力工具化,从而贬低了她们。
我们很难想象出比生孩子和打仗这二者更为迥异的人类行为。但是,印度的那些代孕的妇女与安德鲁·卡内基在美国内战中雇用来代替他的士兵却有着共同之处。对这些情形的正当性的思考将使我们直面那两个将两种不同的正义观念区分开来的问题:我们在自由市场中所做出的选择到底有多自由?是否有一些特定的德性和更高的善是无法在市场上受到尊重的,并且是金钱不能购买的?



迈克尔·桑德尔著 朱慧玲译
☟轻戳「阅读原文」即可参阅获悉更多法学智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