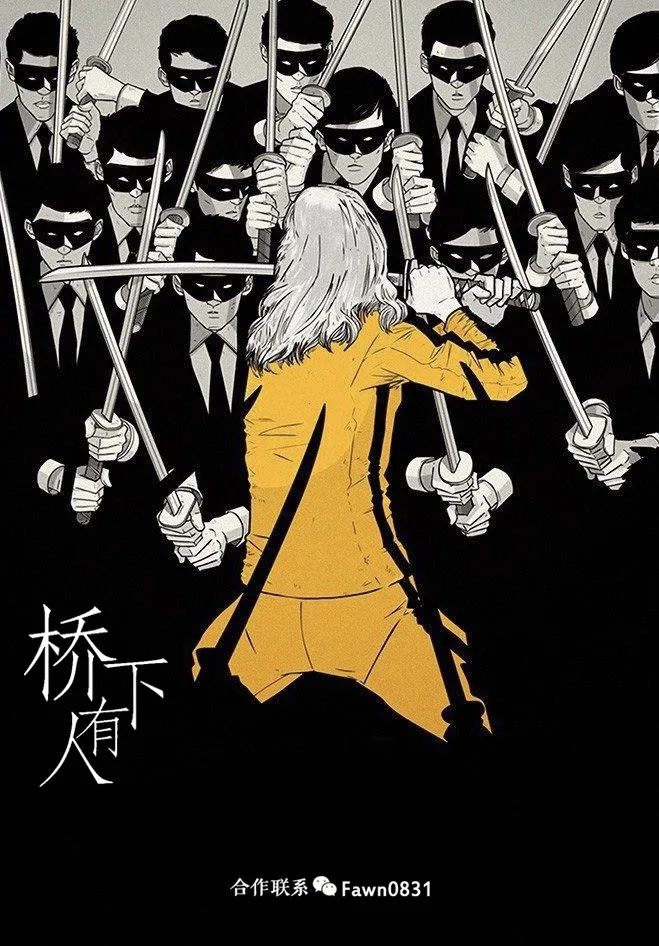1
人对故事的需求,与生俱来。文字被发明后,故事开始广泛流传,步步迭代,最后凝结成了小说。中国人一直有看小说的习惯。
作家止庵家里,每个人都爱看书,拿书当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普通人基本搞不到什么书,无书可看。止庵邻居家弄来一套《水浒传》,他特别想看,但又和人不熟,开不了口,最后,瘾大难忍,他紧着头皮敲门去借。借了还,还了借,前后一共看了三十多遍。
就这么玄。出版人钱伯城聊过一个事,当年想买《水浒传》和《红楼梦》,都得通宵排队,小说一度成了硬通货,那会儿木材很值钱,谁要是有《水浒传》,可以直接到乡下换木材。
止庵可舍不得拿书换木材,精彩的故事,给个黄鹤楼也不换。一次,他的一个朋友托关系借到了很难搞的《基督山伯爵》,压了一块手表,说好只能借三天,七十二小时。
这七十二小时里,朋友家要看一遍,朋友的朋友家也要看一遍,轮到止庵家,只剩二十四小时。这二十四小时里,止庵全家人歇书不歇,打车轮战,止庵为了抢时间,别人吃饭,他不吃,一直看,真正的拿书当饭。
到了八十年代,全民阅读的盛景扑面而来。人们日常看的都是纯文学杂志,《收获》和《当代》是家常便饭。年轻人搞对象,聊的也是小说。当时流行在报上登征婚启事,想提升回信率的话,只需加一句,「喜欢文学」。
九十年代我上了小学,开始认字。家里已经有电视了,但小说并没有退场。我爷爷家沙发上常年躺着一本讲包公断案的话本小说,不是白话文,还在上小学的我经年累月地看,一使劲儿,最后竟给看懂了。我爸不爱看包拯,他的小说圈子里,当时正倒着一本最新尖货。
那天晚上很黑,我爸步行去一个朋友家借那本尖货,我也跟着。九十年代的小镇路灯不多,晚上八九点,照亮全靠月亮。那人家住得很远,我们踩着月光走了很多路,拐了很多弯,但并不觉得是在走弯路,全程满怀期待,从油路一直走到土路,终于到了。
那人从屋里把书递出来,我爸接住以后身上都开始放光了,回去时的路也没那么黑了。书很厚,我扫了一眼书皮,四个字,《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其实我熟,当时我们班上正传阅着一本《天龙八部》的漫画,香港的黄玉郎画的,所以我第一次见识六脉神剑,是在漫画里。再后来,TVB 开始接管时代,95版《神雕侠侣》和97版《天龙八部》从天而降,以更直给的方式,让大家记住了蛤蟆功和降龙十八掌。
2
我意识到,小说正在开始以各种形式向外扩散,好故事不再局限于文字间,大家有了更多享受故事的途径和手段。
这些手段里,最让人失魂落魄的就是电脑游戏《金庸群侠传》,这个经典 RPG 游戏奠定了一代小学生的国学基础。玩《金庸群侠传》那几年,我把所有花钱的爱好都戒了,全部积蓄都给了黑网吧老板。
我现在还没忘十级野球拳的恐怖伤害,还有那耗尽老命组成的梦幻阵容。带着一支同时拥有乔峰、张无忌、令狐冲、段誉、杨过的队伍到处打架,那种感觉,没法儿跟外人说。

2000年后,进入互联网时代,美剧来了。我上大学时,最红美剧三件套是《越狱》《迷失》《英雄》。当时看完就上豆瓣、钻贴吧,看网友分析完再找朋友一条一条过,看美剧用的全是高考的劲儿。
那会儿看美剧的心情和搞对象差不多,心心念念,天天想见,每周就等那一集。陈丹青也爱看美剧,他说过一句话:美剧是二十一世纪的长篇小说。

其实就算是在美剧大杀四方的年代,也依然有很多人沉醉于通过文字享受故事的过程,在争夺人类时间方面,网文可能是唯一可以和美剧对打的内容形式。大部分人其实没怎么看过网文,觉得普遍都是意淫加粗制滥造,对网文有很深的刻板印象,这肯定不对,任何一个行业,都有顶级高手。
众所周知的读书人史航有一个众人意想不到的身份,他是一个资深网文读者。有一次史航录播客「大内密谈」,聊阅读,中间聊到了他看网文,主持人相征惊了,问他,你还看网文啊。言下之意,偏见已然流了一地,这也是大部分人对网文的正常反应。
光付费的、完本儿的网文,史航就看过一百本以上。要知道,现在的网文,动辄就几百万字。
史航说好多写网文的作者,他们对历史的感情,比那些瞧不起网文的职业作家深得多、高级得多,无论修养还是赤诚程度。「他们很多写历史,写穿越的人,并不是为了意淫,他们基本是看破红尘补红尘。大量地写历史,都是为了挽回」。
史航说他读书其实没有鄙视链,「只要你搞得定我,我就服你」。中国的网文,不止搞定了本国人民,还浩荡出征拿下了老外。
3
网文 IP 不断破圈,然后也像当年的金庸小说一样,被改编成了影视剧,以另一种形式呈现故事,甚至一路攻城略地,开始从美剧手里收复失地,抢回了越来越多的观众。
《庆余年》也被拍成了网剧,火遍全国后一路杀到海外,在 YouTube、美国视频网站 Viki 等平台都拿到了超高评价,被翻译成了十几种不同的语言。众多 Viki 网友纷纷留言写下长篇大论,分析剧情,揣测人物,苦思五竹的身份,感叹剧情的玄奇,就像当年一起追《迷失》时的我们。《庆余年》在 Viki 播出后用户评分高达平均9.7分,满分10分。
「我这十年大量地重复看网文,有时候你隔两年再重看《庆余年》,有一些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要重读。」史航喜欢的网文作者有很多,猫腻就是其中之一,猫腻的小说他全看过。
猫腻当年在四川大学电力系上本科,因为不喜欢上学,退学了。回家后开始在网上写小说。2007年五一劳动节,猫腻开始连载自己的第三部小说——《庆余年》。第二年,《庆余年》总点击率过了2000万,风行全网。
猫腻的小说里有情怀,有干货,他让很多人对网文这个品类肃然起敬,偏见消除。北大中文系教授邵燕君评价猫腻是「中国网络文学大师级作家」。
《庆余年》小说开始连载后,横扫网络,收获一大批读者,腾讯集团副总裁、阅文集团CEO、腾讯影业CEO、腾讯动漫董事长程武就是其中之一。2008年到2009年,程武在Google负责市场方面的工作,每天白天上一天班,晚上八点下班后还有别的活儿要干,在这紧紧缩缩的一天里,他使劲儿挤出时间来,就干一件事,看《庆余年》。
2015年,「腾讯影业」成立,程武想基于优质IP来做开发,《庆余年》不出意外成了首选。2017年6月,程武宣布腾讯影业已经获得小说2018年后的影视改编权,并将携手新丽传媒,要把《庆余年》改编成多季的影视作品,书迷嗨哭了。
男主范闲最终落给了张若昀。张若昀被主创团队的激情打动了,觉得他们特别珍惜这个项目,「就是一个有价值的IP遇到了一群狂热的主创分子」。

《庆余年》剧版导演孙皓说这个戏让他感受到特别难得的劲头。这难得的劲头吸引了很多人加入。
《庆余年》小说刚开始连载后,书粉们心里定死的庆帝就是陈道明。剧集筹备阶段,制片方就去找了陈道明,但陈道明一听又是演皇帝,直接拒绝,他早演烦了。主创们一再保证,这个皇帝不一样。最终,成功请陈道明出山,要知道这是他时隔7年再度出演电视剧。在众人的努力下,《庆余年》成了男频IP改编的分水岭,一战登顶。

腾讯影业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庆余年》系列化季播的规划,第一季拍了七个月,第二季在去年10月已经宣布启动。连续将几年时间都交给一部剧,张若昀不觉得亏,这样的团队、这样的故事,值。程武也觉得值。「让内容创造美好,这件事让人快乐」。
4
好内容,藏不住。在2017年胡润原创文学IP价值榜上,《庆余年》排名76,在他身后的,是《赘婿》,位列77。谁也想不到,几年后,这两个当时排名并不靠前的 IP 会炸穿全网。腾讯影业和阅文几乎是同时定下了要影视化《庆余年》和《赘婿》。
《赘婿》这次完全放手给年轻团队去做。在剧版《赘婿》策划阶段,年轻的主创团队就定下一个改编内核:不再考虑男频女频的问题,就一个方向,把这个 IP 做成大众向的,好看的东西,不再去刻意打某个特定群体的喜好。

《庆余年》的故事是从历史虚构时空设定上拔地而起的,《赘婿》不一样,他有很强的现代性,有很多普通人日常熟悉的商业元素和生活地气。
比如拍拼刀刀那场戏时,美术最早放的是一个巨大的超现实转盘,导演一看就不对,得换成苏家布行里可以找到的东西,要客观实际,「通过这些细节让观众觉得,他是一个现代人,带着思想到了古代,并不是在创作上开金手指,无厘头地拿出很多现代的道具」。
《赘婿》的改编从头到尾都因地制宜,配乐尤其突出。主创为每个人物设定了专属 BGM,宁毅有定制的特工 BGM,苏檀儿一出场就起弦乐,吉吉大王标配贝斯和鼓。基本上,闭眼看《赘婿》,也能做到听音识人。

《赘婿》小说也是巨型体量,原著有五百万字,格局很大,如果实打实来拍,还原所有情节,故事推进会很慢,最终出来的未必是大家爱看的东西,编剧团队为了消化好这个 IP,也做了不小的手术。同时,幸好,郭麒麟来了,「赘婿」一入赘,一下就点活了整个项目。
《赘婿》最后也从国内火到国外,如水银泻地点爆网络。以前我们追美剧,现在老外看《赘婿》。
追剧这件事,其实很多人从小就在干。我上小学时,追过一个电视剧,叫《年轮》,讲的是一代知青的人生史诗,时间跨度很长,按道理我看不懂,但我年少早慧,一使劲儿,就又给看懂了。我追得上瘾,每天放学早早开始写作业,就为了晚上能邀功蹭我妈的电视,一起追《年轮》。
《年轮》也是小说改编的,原著作者是梁晓声。梁晓声前几年出了一部新小说,叫《人世间》,全身心投进去写了三年,写下一百一十万字,拿了茅盾文学奖。《人世间》从七十年代写到现在,又是一部大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的生活史,我爱看,毕竟从小就好这口。当然,这种年代史诗小说,改成电视剧是最合适,也最好看的。
想什么来什么,三年多前,腾讯影业和李路导演所在的弘道影业一起找到了梁晓声,表达了要把《人世间》改编成剧的意向。梁晓声说他是个不能与时俱进的人,觉得网上的剧不靠谱,一上来他是抗拒的,「但真正接触了腾讯影业的程总、新丽的曹总之后,发现他们对现实主义还是很有情怀的」。

程武说,为了拿到《人世间》的影视版权,他们的团队足足在版权方那儿蹲守了一个月,最终才拿下《人世间》长达八年的影视版权,那一刻,他松了一口气。
5
《庆余年》《赘婿》《人世间》背后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三驾马车」。「三驾马车」说的是腾讯影业、新丽传媒、阅文影视,三者有各自明确的定位和发力方向。这三部作品,都是「三驾马车」共同打造的。
腾讯影业主投主控,枢纽引擎,新丽传媒聚焦头部,打造精品,阅文影视立足网文,输出内容理解力,并进行IP协同开发。三车并驾齐驱,发挥各自优势,打通生产链路, 业务联动逻辑更为紧密,IP 构建效率得到质变级提升,不辜负每一部好作品。
火力全开的「三驾马车」背后,是腾讯新文创。
2011年,程武在中国动画电影发展高峰论坛上,首次提出「泛娱乐」构思,这一理念在2018年升级为「新文创」——以 IP 构建为核心的全新文化生产方式。目前,「新文创」已经成为腾讯在文化维度的核心战略。
十年下来,「新文创」生态已涵盖文学、动漫、影视、音乐、电竞、游戏等多种文化形式,多重发力,多点开花,实现了《庆余年》《一人之下》《王者荣耀》等原创IP的培育,也通过「数字故宫」、「云游敦煌」等合作让经典文化IP焕活,走进千家万户。
围绕 IP 开发和转化,「新文创」已经构建起了一个极具活力的内容生态。程武认为,在最终目的层面,新文创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人的福祉,新文创会继续以技术赋能人,以服务培育人,以作品滋养人。
一句话,新文创,就是要让好内容以各种形式呈现在大家的日常里,融入到大家的生活中,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