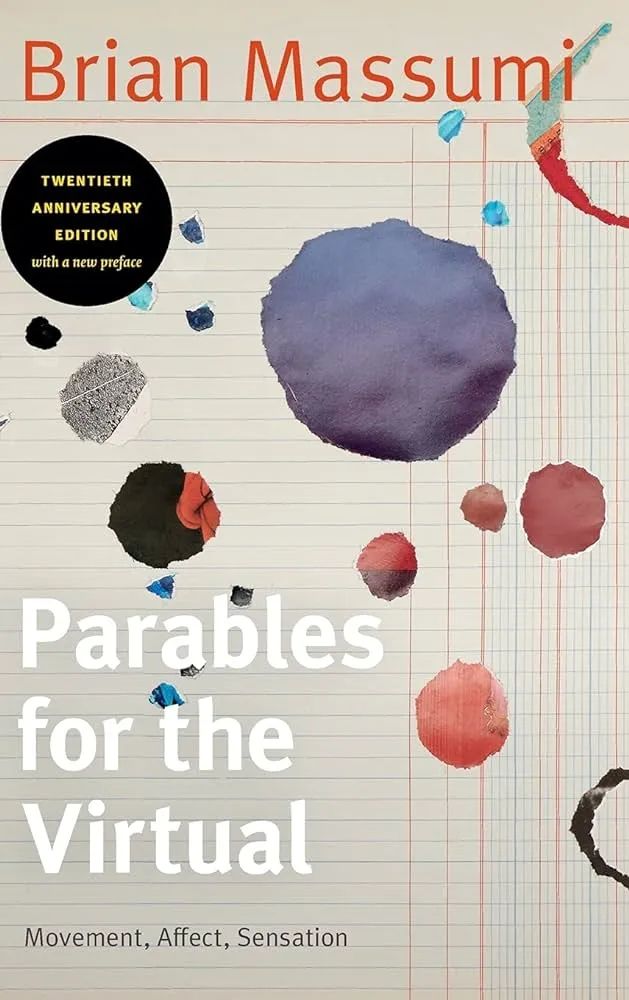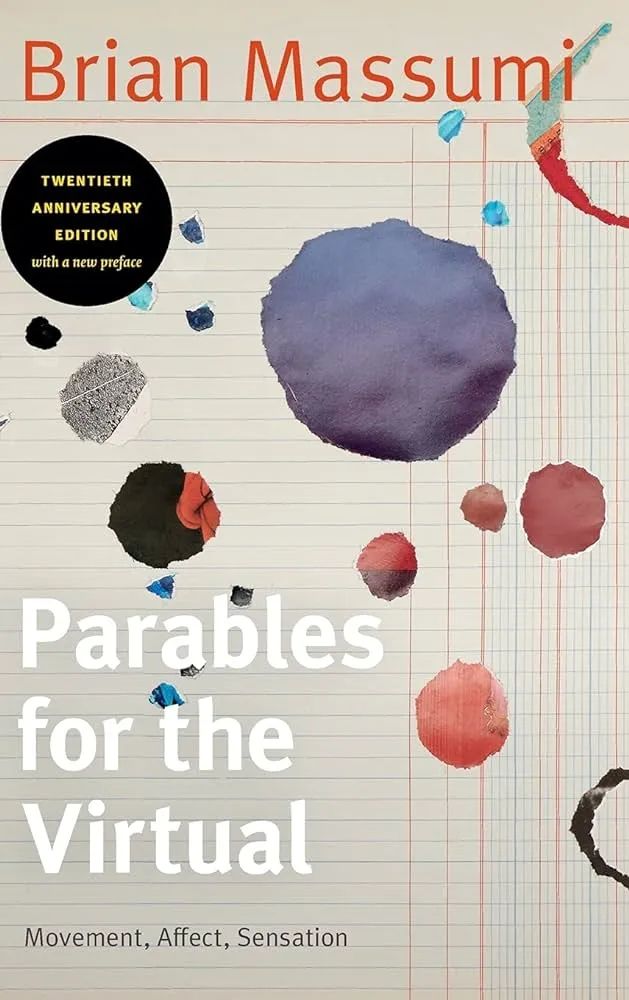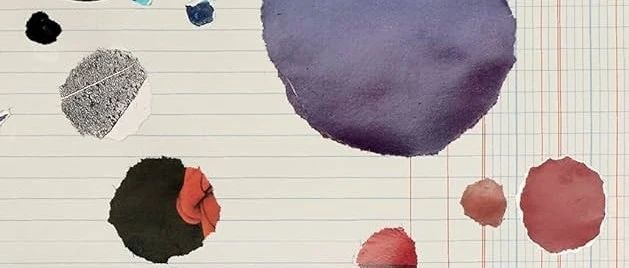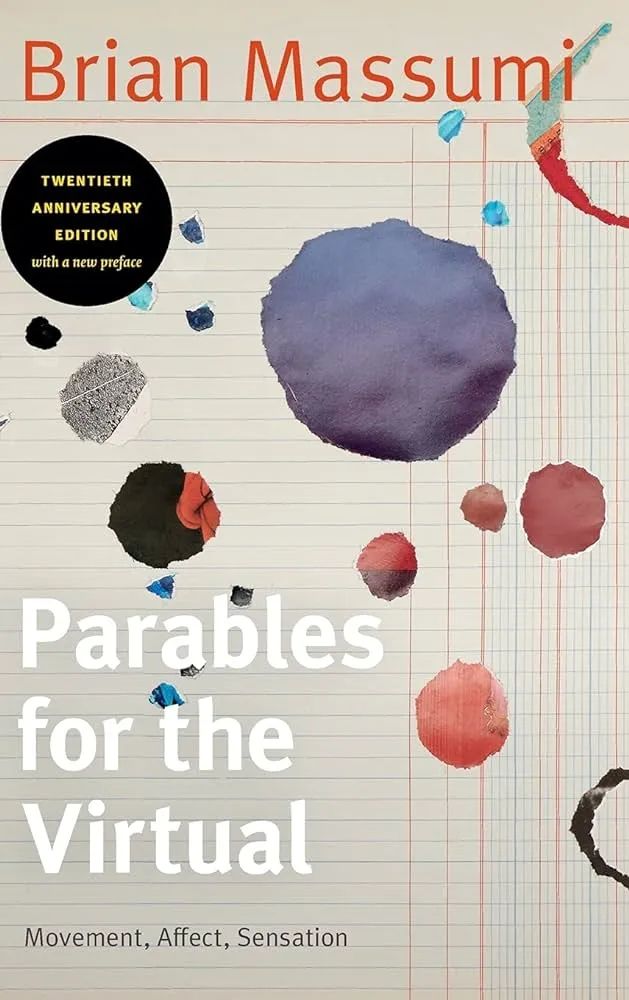
虚拟物的寓言:运动、情动、感觉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
作者: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蒙特利尔大学文理学院传播学系)
译者:陈荣钢
来源:同名著作(杜克大学出版社,2002)导论(节选自1-5页)
当我思考自己的身体,并探讨它如何配得上“身体”这一称号时,有两个方面尤为重要。它会运动,也会感知。这两者同时进行。它随着感觉而运动,同时也感知到自己的运动。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的联系,即运动和感觉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否还能真正理解身体呢?
当我们考虑运动和静止之间的内在联系时,即便是最微小、最细微的位移也能引发质的变化。这是因为身体的行为直接唤起一种感觉,而这些感觉以一种错综复杂、相互共振、相互影响、相互强化的方式展开,这些过程在行动中再次展现,而且通常无法用量化方式来准确描述。质的变化关键在于变化本身。变化可以感知,但也不可预测。
本书旨在深入探讨身体(运动/感觉)与“变化”这一简单概念在文化理论中的影响。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文化理论更倾向于将中介术语及其非中介性联系放在次要地位。这种做法严重忽略了这两个外部问题,尽管它们一直备受关注(可能是人文科学的核心焦点)。由于担心陷入“天真现实主义”(naive realism),即一种还原的经验主义(a reductive empiricism),将文化领域的特殊性消解为表面的、看似毫无问题的“在场”(presence)的哑巴行为。
与壮观的周期性“断裂”相比,持续性质变显得相对苍白。在这种可能性下,日常生活仿佛静如止水。在“中介”(meditation)机制的运作中,文化填补了方法和系统变化之间的空白。这些都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它们建构了物质之间的哑巴式互动,并根据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表意方案使其可读,而人类主体则被“询唤”(interpellated)于这种表意方案中。
尽管中介与权力紧密相连,但它也让日常生活重新获得了一种运动性。即使日常生活可能不再是断裂或反抗的场所,就像在某些特殊历史时刻中所能看到的那样,它仍然可能是适度抵抗(resistance)或颠覆(subversion)的场所,保留了系统性变革的可能性。
这些都是“解读”(reading)或“解码”(decoding)的实践,与主流意识形态计划的事物相悖。身体被视为这些日常抵抗实践的核心。但这种完全中介化的身体只能是一种“话语”身体:一种带有符号手势的身体。符号手势具有意义。如果“表演”得当,它们也可以通过扰乱已经存在的意义而使其失去意义。
无论是否有意义,它们都缺乏感觉。对于它们的描述来说,感觉完全是多余的。更糟糕的是,感觉对其描述具有破坏性,因为它适用于非中介的经验。非中介的经验预示着一种危险,如果说有什么比天真现实主义更可怕的,那就是它的两极对立面——天真主观主义(naive subjectivism)。
早期现象学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感知身体的研究,因为这类研究很难迎合对“文化结构”的新理解,也很难迎合“权力的行使”和媒介生活中存在的反权力迹象。所有这些都涉及到一个没有主观主义的主体:一个由外部机制“构建”(constructed)的主体。
“身体”主体究竟是什么?它不仅仅是身体运动的经验,还是遵循外在方法的主体定位。主体形成的意识形态话语强调了系统结构。对系统的关注必须回归到现实,以便考虑到当地文化差异及其可能蕴含的抵抗实践。为此,“定位”(positioning)的概念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统治结构对主体形成进行标识,这通常被视为“编码”(coding)。编码反过来则被认为是在网格上的定位。网格被视为文化建构意义的对立框架,如男性与女性、黑人与白人、同性恋与异性恋等。身体对应于网格上的一个“位置”,该位置由每对术语中的一个术语重叠而成。身体通过“位于网格上”来定义。这种模式的支持者经常提到,这种模式能够将身体场所与文化“地理学”联系起来,从而缓和意识形态的普遍化倾向。
诚然,位置具有多样性。但它们是否总在一个总体定义的框架内进行组合排列呢?包括所有文化场所中的“颠覆性”在内的可能性是否都被预先编码到意识形态的主结构中了呢?与特定主体定位相关联的身体,难道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局部表现吗?变革的潜力在哪里?
定义框架不仅对身体的“建构”负责,而且似乎还规定了每一种可能的符号化和反符号化动作,将其作为在一套有限的预设条件下可能的排列组合中的选择。那么身体如何能够摆脱这种定义框架呢?网格本身如何变化?系统精确决定的东西如何能够转变为在系统层面发挥作用的关键角色?
定位模式的目的是为了打开一扇窗,使得以变革为名的地方抵抗成为可能。然而,变革问题又卷土重来。由于每一个主体都是如此确定的地方性主体,它被框定在文化地图上的位置,并且形成了僵局。
定位的概念首先从画面中减去了运动,将身体置于文化定格中。解释的起点是精确定位,是停滞的零点。当任何形式的定位成为决定性的第一要素时,运动便成为问题的第二要素。在一切都被符号化和定位之后,如何将运动添加回画面中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但是,在静止中加入运动就像一个数字乘以零得到正积一样容易。当然,在网格上占据一个位置的身体可能会成功移动到另一个位置。事实上,某些规范性的进展,比如从儿童到成人的进展,已经被编码进去了。但这并不能改变如下事实,即定义身体的并不是运动本身,而是运动的起点和终点。运动完全从属于它所连接的位置。这些都是预定义的。像这样增加运动根本不会增加任何东西。你只会得到两个连续的状态:零的倍数。
运动本身缺乏质变的概念。有“位移”,但没有转换,就好像身体只是从一个定义“跳跃”到下一个定义。由于位置模型的定义框架是瞬时的(punctual),它根本无法将现实归纳为间隔(interval),而间隔的交叉是一种连续性(或什么都不是)。交叉的空间,即网格上各个位置之间的空隙,属于理论上的无主之地。
身体“质的运动”同样缺乏,它直接关乎作为符号的感觉。此外,物质(无论是身体的还是其他的)都从未在我们的论述中出现过。尽管许多相关方法都自称为唯物主义,但物质只能间接地进入——作为中介。
这个研究项目始于近十年前,以应对这些问题。它基于一种希望,即以物质为载体的运动、感觉和经验可以通过文化理论来思考,既不会陷入天真的现实主义陷阱,也不会陷入主观主义的困境,更不会与后结构主义文化理论的真实见解相矛盾。这样做的目的是将物质无中介地放回到文化唯物主义中,同时将最直接的肉体放回到身体中。
在理论层面上,我们需要与作为编码概念基础的语言模式(通常索绪尔式的灵感加拉康式的拐点)分道扬镳,并找到一种愿意与连续性打交道的符号学,这是皮尔斯创始时关注的主题。这并非反对“理论”或“文化研究”,而是希望在其成就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或许能够从被忽视或未充分重视的源头中注入新概念,刷新词汇。曾经我认为这种刷新是为了恢复经验的“具体性”,但很快就摒弃了这个想法。
以运动为例,当物体运动时,它与自身不重合,而是与自身的过渡相吻合,即自身的变化。在任何特定的运动中,它所能涉及的变化范围都是不存在的,更不用说经过的“位置”了。在运动中,一个物体与其自身不存在的变化潜能处于一种直接、展开的关系。用吉尔·德勒兹的话说,这种关系既真实又抽象。位置网格是抽象的,尽管其目的是将文化理论拉回到地方层面,因为它涉及到一个总体性的定义网格,其确定性先于它们所构建的身体或应用的身体而存在。
与德勒兹的“真实但抽象”的抽象性截然不同,这种抽象性并不预先存在,与中介无关。如果意识形态必须被理解为中介,那么这种“真实–抽象”就不是意识形态。在这里,抽象的意思是永远不存在于位置中,只是顺带出现。这种抽象性与现实关系的直接性有关,即身体与其自身的不确定性的关系。
身体承载的不确定性与身体密不可分。身体存在一个非肉体的维度。它属于身体,但又不属于身体(真实的、物质的,但又是无形体的;不可分割、重合,但又互不关联)。如果这是“具体的”,那么最初启动的项目就会出现严重的曲折。
要理解“真实、物质但无形体”的含义,一种方法是将其看作对于作为定位事物的身体而言,就像能量对于物质一样。能量和物质是同一实在的相互转换模式。这将使无肉体成为通常意义上的身体的位移,但不是时间上的移动。它是身体的转换或展开,与身体的一举一动同步,始终伴随。
这种自析取的重合将本体论的差异融入到身体的核心。身体的变化潜力与身体作为多样性属于同一现实,但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整合运动使我们直接陷入米歇尔·福柯所说的“无形体的唯物主义”(incorporeal materialism)。这种运动的滑移给本体论和本体论差异的问题带来了新的紧迫性,这些问题与潜力、过程以及事件的概念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以一种将“存在”(being)直接转化为生成的方式。再次解释德勒兹,文化和文学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模型的问题并不在于它们太抽象而无法把握现实的具体性。问题在于它们不够抽象,无法掌握具体的真正“无形体性”。
当阐述通道和位置的悖论时,哲学上的前驱是柏格森(Henri Bergson)。滑入非唯物主义的情境遵循柏格森对芝诺(Zeno)运动悖论的著名分析。当芝诺出射他的“哲学之箭”时,他以常识方式思考飞行轨迹——箭依次占据的一系列点或位置构成了线性轨迹。问题在于,在线上的一个点和下一个点之间存在无穷多个中间点。如果箭占据路径上的第一个点,它将永远无法到达下一个点,除非它占据介于两点之间的每一个无穷点。当然,无穷的本质是永远无法到达其终点。箭被吞没在过渡性的无穷中。它的飞行轨迹崩溃。箭被固定住了。
如果说箭移动了,那是因为它从未停留在任何一个点上。它在穿越它们的过程中。从弓到目标的过渡不能分解成“组成点”。路径不由位置组成。它不可分解,而是一个动态的统一体。
这种运动的连续性属于不可测量、不可分割的现实秩序。它不会停止,直到它停下来——当它击中目标时。然后,只有在箭击中目标后,箭才处于位置上。只有在箭击中目标后,其真实的轨迹才能被描绘出来。这些点或位置在运动结束后才出现。
在我们的思考中,我们仿佛沿着路径放置了目标。介于中间的位置是逻辑上的目标,一个可能的终点。箭的飞行并非芝诺所认为的“被固定住”。当我们将其运动解释为可分解为位置时,我们在思想中止住了它。柏格森的观点是,空间本身就是这种回顾性构建的一种形式。当我们将空间看作是“广泛的”(可测量、可分割),并由描绘对象可能占据的点组成时,我们在思想中止住了世界。我们放弃了它的动态统一,放弃了它运动的连续性,因此我们只看到现实的一个维度。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