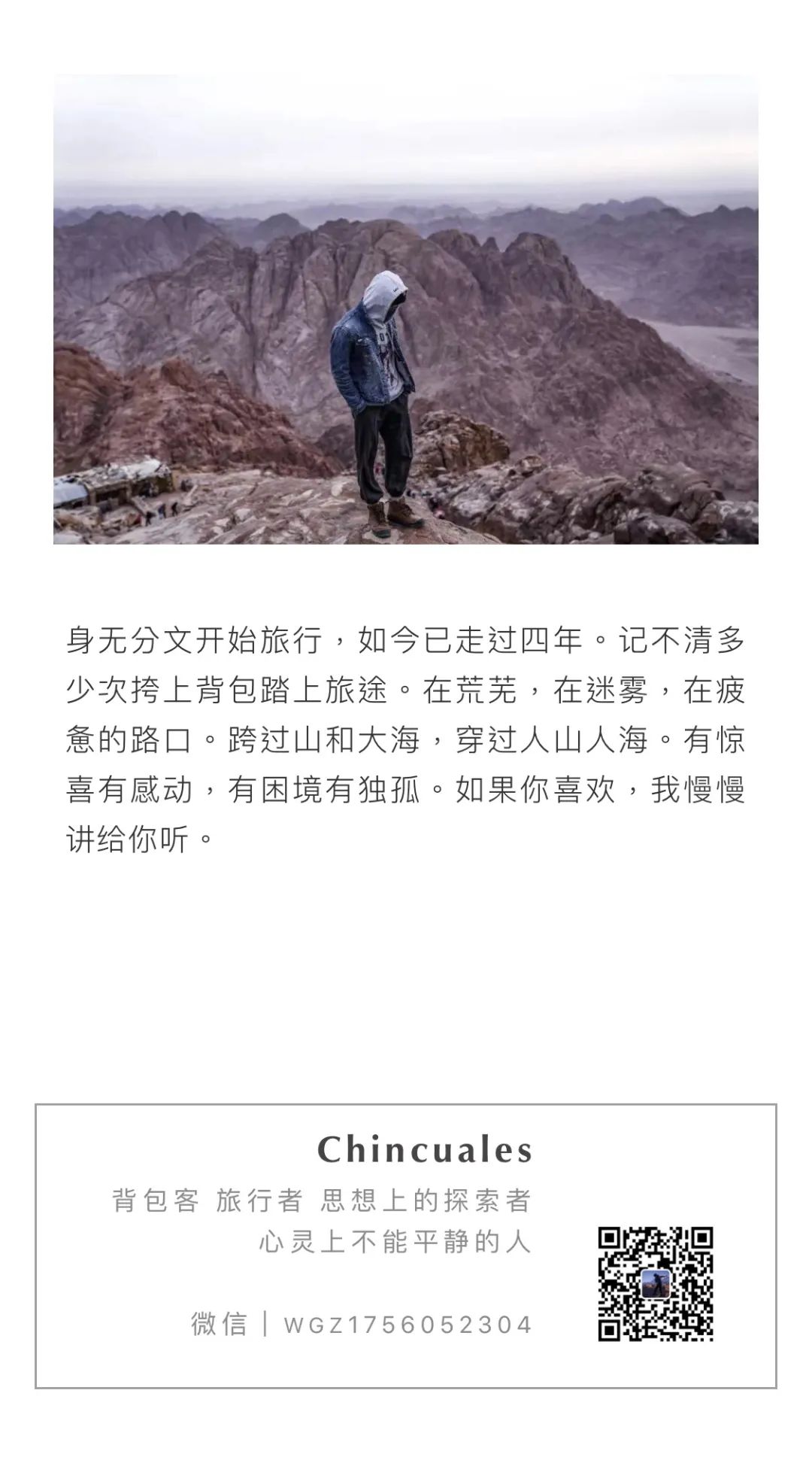锡格纳吉整个小镇几乎都被山林草木覆盖包围,清晨的阳光把万物的影子拉长,那样的时光我喜欢把焦点对准我路过的每个事物,甚至叶子的脉络。并非单一地对那些事物感兴趣,而是惊叹于人的眼睛竟能把万物看的那么清晰,好像连细胞都看得一清二楚,我感叹我能被赐予那么出色的视力,也感恩于太阳的如期而至。
我慢跑在山间的柏油路上,四周都是高耸着的我已忘了名字的树木,格鲁吉亚的大叔赶着牛群从远处走来,古典的英伦风,脸颊自带高原红,或许是起床就喝了杯自酿的葡萄酒。相逢时他向我竖起了大拇指,我头一次觉得跑步也能获得别人的尊敬。
这是我骑行泸沽湖时不由自主地从我脑海中蹦出的画面。我还想到亚美尼亚清净的公路上那些老式的奔驰车,开满雏菊的梅斯蒂亚,埃里温为我打热水的姑娘,还有结满苹果和核桃的巴基斯坦HUNZA。
这些过去的画面在我骑行泸沽湖的时候突然毫不留情地从我记忆的底层冲了(自主)出来,其实我还想到了更多,只是落到笔上那些画面便又沉入了记忆的深渊。有时候我很怕,害怕那些画面再也不会涌现,害怕记忆空空。
总之这些画面的出现的时刻,我觉得自己是个饱满(精神上)的人,不再两手空空。
我是在女神湾的傍晚想起锡格纳吉的。摩梭大叔牵着两头羊从泸沽湖边的碎石滩走过,两边是高大的叶子已经黄了一半的杨树。我坐在那些碎石组成的长滩上,等待日头消失。女神湾的黄昏仿佛就是“惬意”本身。那里有点像海,高大的杨树长在水里,狭长幽暗的小路仿佛通往格鲁吉亚的某个小镇。

猪槽船幽幽地漂在湖面上,悬在峰顶的云已经熟透开始慢慢散去,就好像梅斯蒂亚的雏菊默默绽放又逐渐凋零,有几颗星已经开始露出锋芒。那时我好像超出时间之外,被隐在那静谧的湖湾夜色中,毕竟这样的时刻人生又会有几遭呢?
唯一的遗憾是当时手里少了一瓶啤酒。
泸沽湖三分之一在丽江三分之二在凉山,属于摩梭人。摩梭人在丽江被归为纳西族,而在凉山则被归为蒙古族,但他们在身份证的民族一栏上写的不是五十六个民族中的任何一个,而是“摩梭人”三个字。
晴天的泸沽湖十分好看,除了山头悬着的似乎终年不散的云,穹顶之下绝无半点斑驳。雨季末,湖里的水性杨花还开着。阿飘告诉我和马达加斯加比起来,这里的云就是弟弟,她还跟我说起那里的粉色夕阳和晨雾中的猴面包树,当然还有便宜得像不要钱似的的牛油果,和几块钱能买一桶的皮皮虾。
不过我想马达加斯加可没有这么美的湖吧。
是日湖面没有一丝波澜,只有野鸭在山峰和云朵的倒影中畅游,整块湖俨然一面硕大的镜子,美得令人惊叹。我总担心会把单车拱到马路牙子上或者摔下悬崖,好在都没有发生。
看到泸沽湖我总会想起伊犁的赛里木湖,那玄幻的蓝色,那长在水里伸到天上的雪山,那进了水的帐篷和续命的大馕。第三天清晨雨终于停了,我拉开帐篷,眼前是金黄的草地,蔚蓝的湖水,冒着寒气的洁白雪山。转身又一看,德霖的帐篷就像一张麻袋皮摊在草地上。德霖你在哪里,我问。几秒后,麻袋皮下面传来了一句“奄奄一息”的声音,彤彤在一边笑。几天下来,茫茫无边的赛里木湖彼岸只有我们三人,最后那天傍晚我们拖着疲惫的身子终于被骑老式摩托巡逻的的哈萨克小哥发现了,他说狼群会经常在夜晚潜入赛里木湖,听后我惊起一身冷汗。我们是逃票加翻越钢丝网(无耻又刺激)进去的。
泸沽湖的女神湾有一家叫“好人小吃”的饭馆,店铺的主人就是个好人,他乐善好施喜好打抱不平,已经收到总数超过两万五千封的感谢信。店铺装修简陋,几处缺瓦的地方用玻璃修补,所以阳光总会在某个时间段穿过玻璃照亮屋里的某个角落。屋顶挂满了写着标语的旗帜,墙角堆着几袋比香格里拉品质更好的风干松茸,这是炖土鸡的主要食材。
“有人曾经花七十万来买我炖鱼的手艺,待会儿你要尝到你这辈子都没吃过的美味鱼汤,要吃出半点腥味儿我给你二十万,旺季的时候每天要招待一千人哟!。”作为尊敬,早上我饿着肚子直到“好人小吃”开门营业。其实头天晚上我就去了只是被撵了出来,他问我你有多饿?我说不是特别饿,然后我就被撵出来了,这也是我没吃早饭的原因。

饭后我彻底相信了他那番轻狂的话语。切段烹炸的新鲜湖鱼肉质肥嫩鲜美,反复煎熬的鱼汤宛如伊犁河谷哈萨克族最醇美的牛奶,我当真从未喝过如此美味的鱼汤。而松茸炖土鸡也实为真正意义上的松茸炖鸡,珍贵的松茸好似不花钱似的塞满了整个铁盆,土鸡滑嫩,汤汁回甘。还有清炒蔬菜和糖拌西红柿。
然而这一切竟然只要40块,饭菜无限量。
湖湾边有一家叫“不二茶坞”的小店,是个刚做父亲的九三年小伙子经营的,以酒水饮料为主,其中的自酿玫瑰酒是小店的主打,口感醇厚味道甘美,我只尝了下,六十多一小壶我是舍不得买的。我去他那里吃过三次扬州炒饭,当真这辈子没吃过如此好吃的炒饭,每次都一扫而空。还有那只加了姜和蒜的面食就像施加了某种魔法,简单却惊奇地美味。当然如果去了一定要尝一尝小伙子自制的酒酿汤圆。
这次骑行我收获了整个泸沽湖还有埋在深处的诸多记忆。
THE PICTURES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