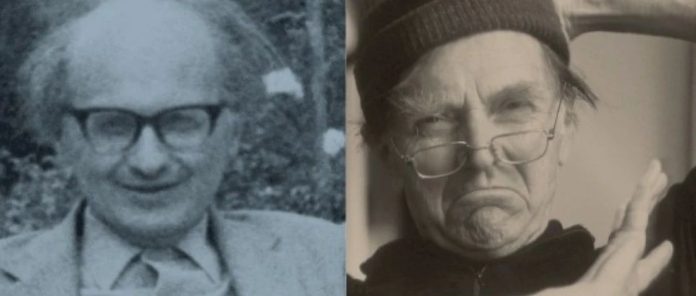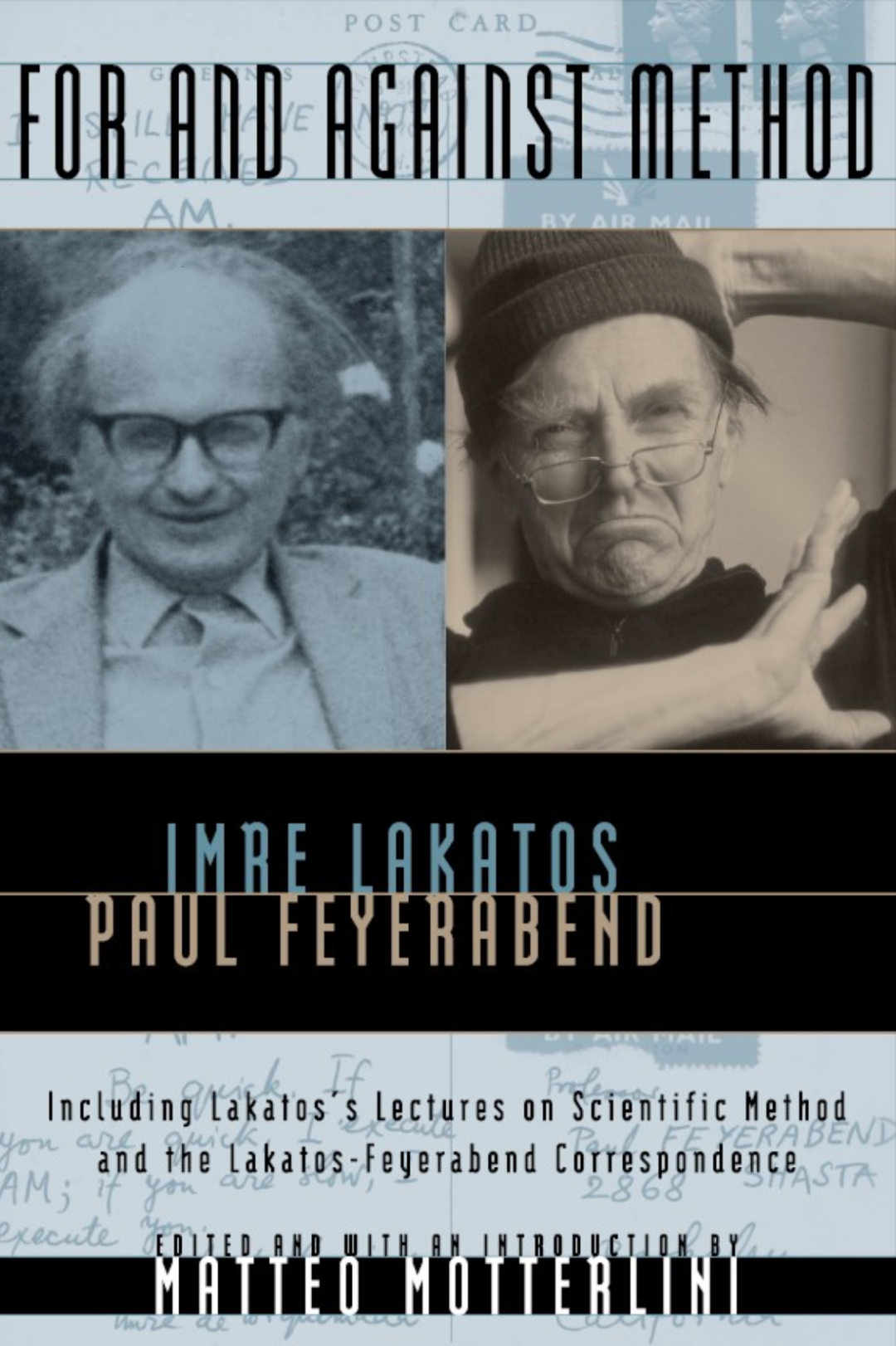
保罗·费耶拉本德(Paul Feyerabend)的《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对费耶拉本德的挑战。据传,在一次聚会上,拉卡托斯向费耶拉本德提出了一个挑战,询问为什么他不将自己的想法写下来。尽管拉卡托斯在撰写答复之前便去世了,但这个挑战激发了费耶拉本德进一步探索科学方法的思考,最终形成了《反对方法》这一著作。这本书不仅从讲座和信件中重建了拉卡托斯最初的反驳论点,而且也为我们展示了费耶拉本德和拉卡托斯两位哲学家在科学方法领域的交锋,展现了他们的智慧和思想的精彩对比。
《赞成与反对方法》(For and Against Method)开篇以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之间的想象对话展开,这是意大利科学哲学家马泰奥·莫特利尼(Matteo Motterlini)基于两位哲学家已发表的作品所构建的内容,旨在综合他们的立场和论点。第一部分记录了拉卡托斯关于科学方法的最后一次讲座。第二部分是费耶阿本德的回应,其中包括他之前发表的一篇关于无政府主义的文章,该文章开篇即对拉卡托斯的立场提出挑战,而后在《反对方法》中继续对其进行批判。第三部分也是最长的部分,包括了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在1968年至1974年之间的信件交流,其中涉及了关于方法以及许多其他问题和想法的讨论,以及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事件。
***
本文译自《赞成与反对方法》(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9)的第二部分,也就是费耶阿本德对无政府主义的论述。费耶拉本德在1973年2月的一封信中,附上了他为计划于同年3月20日举行的一次会议起草的草稿论文,他计划在会上从无政府主义者的角度批评拉卡托斯对“法律与秩序”的辩护。该论文经过稍加修改之后也曾收录了费耶拉本德1975年(175-81页)和1996年(第一章)出版的著作中。过几天还将推送本书收纳的拉卡斯托的讲座《科学标准的神学性质》(The Theological Nature of Scientific Standards)(31-40页)。
***
无政府主义反对现存秩序,它希望摧毁这个秩序或逃离它。政治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政治制度,宗教无政府主义者可能反对整个物质世界。他们将政治制度和物质世界视为较低层次的存在,并希望消除它们对自己生活的影响。两者对什么是“真”、“善”和人类价值持教条主义观点。
例如,启蒙后期的政治无政府主义者信仰科学和人类的自然理性。消除所有界限,自然理性找到正确的道路。取消教育方法,人将自我教育。消除政治制度,人类将组成代表他们“自然倾向”的团体,从而成为和谐(非异化)生活的一部分。
科学信仰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科学在17世纪和18世纪扮演了革命性的角色。当无政府主义者扬言毁灭时,科学家们打破了早先时代的和谐世界,他们消除了毫无结果的“知识”,改变了社会关系,并慢慢地汇集了一种新型知识的要素,这种知识对人类来说既真实又有益。
如今,人们天真而幼稚地接受这种科学,甚至阿尔都塞(Althusser)这样的“进步”左派也愿意接受。这种接受态度受到两种事态发展的威胁——其一,科学从哲学探索转变为商业事业;其二,有关科学事实和理论地位的某些发现也威胁着这种幼稚的接受态度。
20世纪的科学已经放弃了一切哲学虚构,变成了一项巨大的商业事业。它不再威胁社会,而是成为社会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人道主义的考量几乎不存在了,不局限于局部改进的进步主义也很少见。对于这些擅长解决微小问题的人类蚂蚁来说,良好的薪酬、与老板和同事之间的良好关系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但他们无法理解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任何事物。让某人迈出一大步,这个行业就会把它变成一个用来迫使人们屈服的棍棒。
我们还发现,科学没有可靠的结果,它的理论和事实陈述都是假设,经常在局部和全局上错误,对从未存在的事物进行断言。根据这个观点,从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On Liberty)开始,到最为激进的当代宣传者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和赫尔穆特·斯皮纳(Helmut Spinner),他们都认为,科学是一系列相互竞争的替代方案。“被接受”的观点是暂时占据优势的观点,要么是因为某种“怪癖”,要么是因为某些切实的好处。革命都要翻天覆地,不可能不改变原则,不触动事实。
外表不悦目,结果不可信,科学已经不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盟友。它已成为一个问题。认识论无政府主义(epistemological anarchism)通过消除早期无政府主义形式中的教条主义元素来解决这个问题。
认识论无政府主义与怀疑论和政治(宗教)无政府主义都不同。怀疑论者可能将每种观点视为同样好或同样差,或者干脆不做任何判断,而认识论无政府主义者则毫不犹豫地捍卫最陈腐或最怪诞的看法。政治无政府主义者想要消除某种生活形式,而认识论无政府主义者可能想要捍卫它,因为他对任何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没有永恒的忠诚或永恒的厌恶。
像达达主义者一样,认识论无政府主义者“不仅没有纲领,而且反对一切纲领”。他们在很多方面都类似,参考汉斯·里希特(Hans Richter)的《达达:艺术与反艺术》(Dada: Art and Anti Art)这本达达主义的优秀教科书。
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会成为现状或反现状的激烈捍卫者:“要成为真正的达达主义者,还必须成为反达达主义者。”他的目标会因为辩论、无聊、宗教皈依经历或是想要给某些人留下印象而保持稳定或变化。在某个目标下,他可能会尝试通过组织团体或独自行动来实现目标。
他可能诉诸理性或情感。他可能决定采取暴力手段,也诉诸和平方式。他最喜欢的消遣是通过为不合理的教义创造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迷惑理性主义者。他不会拒绝“荒谬”或“不道德”的观点,他眼里也没有什么必不可少的方法。他唯一绝对反对的是普遍标准、普遍法律、普遍理念,如“真理”、“正义”、“诚实”、“理性”及其所引发的行为,尽管他不否认,按照这样的法律(这样的标准、这样的理念)行事并相信它们往往是明智的。
他可能在反对科学、常识和被两者所检验的物质世界方面接近宗教无政府主义者。他可能在积极捍卫科学纯洁性方面胜过任何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所有这些愤怒的背后,是他的信念。只有当人类能够超越最基本的信念,包括超越那些号称使他“成为人类”的信念时,他才会停止成为奴隶,获得一种谨慎从众的行为,而且是有尊严的行为。
汉斯·里希特写道:“理性与反理性、意义与无意义、设计与机缘、意识与无意识(以及我想补充的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都属于整体的必要部分——这是达达主义的核心信息。”认识论无政府主义者可能会同意这种观点,尽管他不会用这样一种受限制的方式表达自己。
阐述完学说之后,认识论无政府主义者可能会试图推销它(他也可能保留给自己,认为即使最美好的想法在开始流传时便会变得陈旧)。他的推销方法取决于听众。如果他面对的是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听众,他将提出一系列论点,试图说服他们,在科学中,他们最欣赏的事物将以无政府主义的方式实现。
他将使用最可能在这类听众中成功的宣传手段——使用论证。他将从历史上证明,并不存在一条一劳永逸的单一方法论规则,也不存在一种永远不会推动科学的“非理性”行动。人类和自然是非常反复无常的实体,如果一个人决定预先限制自己,就无法征服和理解它们。
他会引用爱因斯坦这样备受尊敬的科学家的言论,比如:“由于经验事实设定了科学家的外部条件,不允许他在构建他的概念世界时过于受到对认识论体系的限制。因此,对系统认识论者来说,他必须称为某种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他会利用这些片段,试图说服听众,凡事皆可为,这是与科学家携手推动科学并采取必要行动的唯一普遍原则。
伊姆雷·拉卡托斯持有不同观点。他承认现有的方法论与科学实践存在冲突,但他认为存在足够自由的标准来允许科学发展,并且足够具有实质性以确保理性的存在。这些标准适用于科学研究项目,而不是单个理论;它们评估一个项目在一段时间内的进展,而不是在某个特定时间点的状态;它们将这种进展与竞争对手的进展相比较,而不是孤立地评价。
如果一个研究项目的预测得到后续研究的验证,并因此带来新的发现,那么它被认为是“进步的”。如果一个项目没有做出这样的预测,而是被迫接受竞争对手的发现,那么它被称为“退化的”。这些标准评价的是研究项目本身,而不是指导科学家应该做什么。
例如,并没有规则告诉科学家要放弃一个退化的项目,因为一个看似退化的项目可能会重新复兴并取得成功。(这种情况在原子论、世界的时间有限性、地球运动等领域发生过。所有这些研究项目都曾多次经历进步和退化,如今,它们都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追求一个研究项目的退化分支也是“理性的”,即使它已经被竞争对手超越。因此,伊姆雷·拉卡托斯的方法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凡事皆可为”之间在“理性上”没有区别。然而,在表达方式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举个例子,伊姆雷·拉卡托斯批评那些处于退化阶段的研究项目,并要求撤销对它们的支持。他的标准允许这种批评,也允许采取行动。然而,他们并不鼓励这种行为,因为也允许相反的情况发生,允许我们赞扬这些项目,并用我们掌握的一切支持它们。
拉卡托斯经常将这种赞扬称为“非理性的”。他这样做时,使用了与自己不同的标准,例如他使用了常识标准。将常识标准(这些标准独立于他的标准之外)与研究项目的方法论相结合,他利用前者的直观合理性来支持后者,并将无政府主义偷偷地注入最虔诚的理性主义者的大脑之中。在这方面,他比我要高效得多,因为理性主义者在无掩饰地提出无政府主义时无法接受这一点。当然,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自己被愚弄了。那将是他们准备好接受纯粹的无政府主义时的一天。
拉卡托斯也未能成功地论证“理性变革”(rational change),库恩(Kuhn)则诉诸于“暴民心理学”(mob psychology)。革命导致对立学派之间的争吵。一所学校想要放弃正统课程,另一所学校想要保留它。正如我们所见,研究计划方法论推荐的标准允许这两种行动。因此,对立学派之间的斗争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正如拉卡托斯所言,库恩是对的。
最后,拉卡托斯并没有证明亚里士多德科学、魔法、巫术不如现代科学。在批判亚里士多德科学(以及其他“伪”学科)时,拉卡托斯使用了他的标准。他是如何获得他的标准的呢?他是通过对“过去两个世纪”的现代科学进行理性重建而获得的。
因此,用他的标准来衡量亚里士多德科学就意味着将亚里士多德科学与“过去两个世纪”的现代科学进行比较。只有在证明现代科学比亚里士多德科学更好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只有在证明(一)现代科学有更好的目标,以及(二)现代科学比对手更有效地达到目标的情况下,现代科学和亚里士多德科学才没有什么可比性。
拉卡托斯没有在任何地方证明,现代科学的目标(借助“心灵的预见”)取得进步比亚里士多德科学的目标(把事实吸收到稳定的基本理论体系中并“拯救”现象)更好,而且达到目标的效率更高。因此,在拉卡托斯那里,科学与巫术的比较仍然悬而未决。
因此,科学和研究计划的方法论都没有提供反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据。无论是拉卡托斯还是其他人,都没有证明科学比巫术更好,也没有证明科学是以理性的方式进行的。是偏好而不是论证指导着我们对科学的选择,是偏好而不是论证使我们在科学中采取某些行动。
我们可能通过偏好做出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决定就是完全理性和可靠的,就像一块美味的肉可能被苍蝇包围和完全覆盖一样。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一结果感到沮丧。科学毕竟是我们的创造物,而不是我们的君主。因此,它应该是我们奇思妙想的奴隶,而不是我们意愿的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