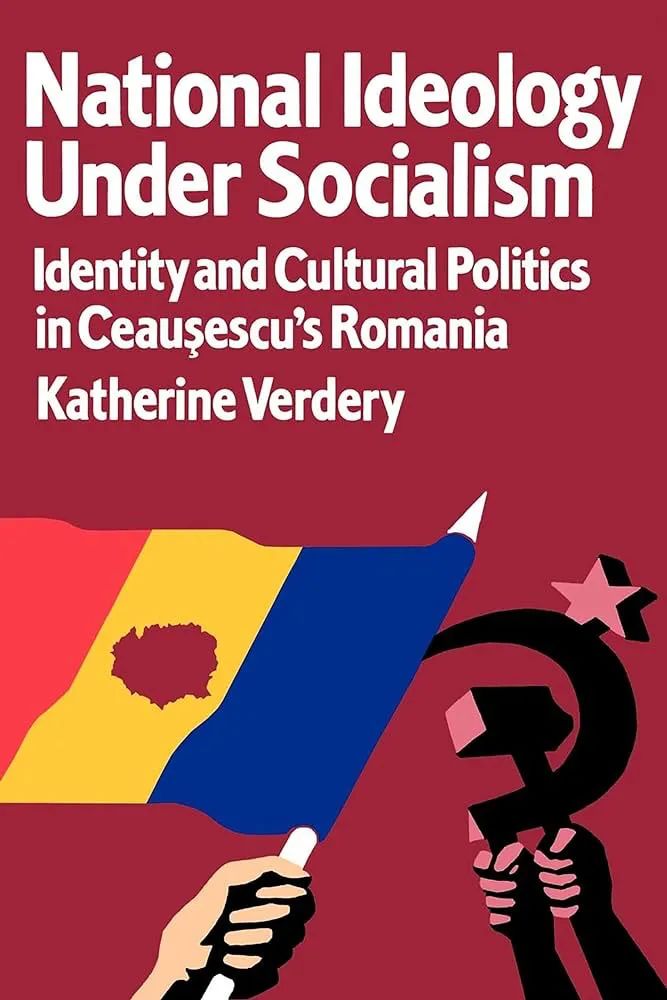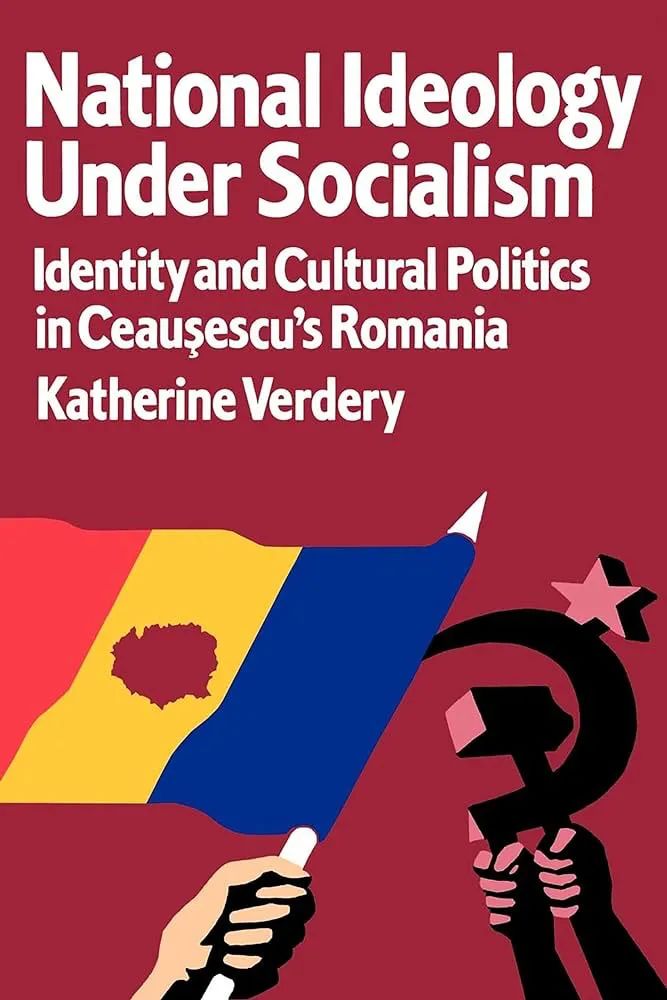
社会主义的民族意识形态: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罗马尼亚的身份与文化政治
National Ideology Under Socialism: Identity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Ceausescu’s Romania
作者:凯瑟琳·维德里(Katherine Verdery,1948- )
译者:陈荣钢
来源:同名著作(加州大学出版社,1995)导论,有删节
一个民族和文明的认同都反映并浓缩在思想创造的产物之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如果这种认同受到灭绝的威胁,文化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热烈、更加重要,直到文化本身成为凝聚人民的鲜活价值所在。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
——米哈伊·迪努·乔治乌(Mihai Dinu Gheorghiu)
1989年3月,六名前罗马尼亚共产党官员致公开信给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抗议他的政策。他们指控道:“罗马尼亚是且一直是欧洲国家……你改变了农村地区的地理面貌,但你无法将罗马尼亚文化变成非洲文化。”一位流亡的罗马尼亚作家对此番言论表示赞同,他哀叹祖国从“意识形态统治”(ideocracy)变成了“愚昧统治”(idiocracy),并批判了“针对能力、智力、才华的粗暴行为,总之,这就是针对文化的粗暴行为”,谴责齐奥塞斯库的个人崇拜是“非洲国家的典型做法”。
其他作家也对罗马尼亚不再是欧洲社会感到失望,他们恳求“欧洲大家庭”帮助罗马尼亚恢复法国大革命的“文明原则”:“罗马尼亚必须再次在欧洲占据一席之地。”一位文学评论家与一位位高权重的作家交锋,他用对手的一句反欧洲言论(“我讨厌法语及其被吹捧的笛卡尔理性主义”)作为论文集的开篇,斥责这种态度是“野蛮的”,并为欧洲文化进行辩护。在罗马尼亚各地,在推翻齐奥塞斯库“野蛮”统治的暴力事件发生期间和之后,示威学生高呼“欧洲与我们同在!”,欢欣雀跃的罗马尼亚人写信给海外的朋友们,兴奋地喊道:“我们终于要重返欧洲了!”
与此截然相反,一位社会学家坚持认为:“(我们的文化)不能一瘸一拐地追随欧洲文明,固守边缘的身份认同……(我们)不是附属文化,通往我们价值观道路的起点并非西方。” 其他人也加入了他的行列,抨击欧洲影响是“知识界的独裁”和“对罗马尼亚文化传统的攻击”。一位评论家谴责了令人无法容忍的、“抵制我们价值观”的行为,他抱怨道:“我们翻译了(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的四本书,却没翻译过(芝加哥罗马尼亚裔移民)米尔恰·埃利亚德(Mircea Eliade)的一本著作。” 1987年罗马尼亚玩具店里出售的棋盘游戏“达契亚人和罗马人”更形象地说明了这些人的观点,该游戏将(“欧洲的”)罗马人塑造成游戏恶棍,对抗(“本土的”)达契亚人。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欧洲和非洲、文化和野蛮、殖民剥削和西方独裁等意象在罗马尼亚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中来回碰撞。齐奥塞斯库反对派青睐的欧洲主义表明,这些意象是激烈而充满狂热的情感表达,浓缩着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反对派已经成为亲欧洲的代名词,齐奥塞斯库及其盟友则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欧洲化导致的民族精神消亡怒斥不已。
这些充满火药味的象征经常出现在政治演讲中,但它们真正成为政治话语核心的是另一个领域——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文化界。在知识分子生活中,文化是生死斗争的“货币”。但由于两个原因,它们在知识分子领域和政治领域之间轻易地流动,一个原因是历史性的,另一个是当代的。几个世纪以来,不同的政治选择一直与罗马尼亚身份的替代或代表(欧洲的、东方的、既不是欧洲的也不是东方的)交织在一起。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之间建立的关系确保文化生活将与政治纠缠在一起。
本书讲述了罗马尼亚身份的意象如何在罗马尼亚政治化的文化世界中相互较量,并由此在声称自己在社会主义的秩序下延续了罗马尼亚的民族意识形态。我探讨创造这些意象的人(不同知识分子群体,或者更广泛地说是文化生产者)之间,以及他们与党的领导层之间的关系。这些不同的群体——作为文化和统治的生产者,书写和讨论着“民族”,将“民族”构建为一个具有政治相关性的话语领域。他们的言论与其他主题的论述乃至更广泛的策略共存,这些策略包括胁迫和明显的暴力。所有这些共同塑造了齐奥塞斯库罗马尼亚的“合法化”或“同意”体系,也塑造了它的转型要素。
以下章节讨论了知识分子对这些过程的贡献,探讨哲学家、艺术家、作家、历史学家、记者等人如何创造和重新创造民族意识形态,探讨这一切发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而不是其他制度下会有什么不同。潜藏在这些问题背后的还有更大的问题。二十世纪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有哪些特质使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民族”这个概念有哪些特质使它成为文化和政治的如此恰当的结合点?最后,民族的话语对试图挪用它的社会主义秩序产生了什么后果?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似乎都关乎一些深奥的议题,关乎社会学家、文学评论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之间的争论。然而,本书的意义远不止于此。首先,正是政治与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1989年12月下旬新成立的政府不仅囊括了共产主义改革派,还包括几位诗人——米尔恰·迪内斯库(Mircea Dinescu)和安娜·布兰迪亚娜(Ana Blandiana)、文学评论家——奥雷尔·德拉戈什·蒙泰亚努(Aurel Dragoș Munteanu)、哲学家和美学家——米哈伊·肖拉(Mihai Şora)、安德烈·普莱舒(Andrei Pleșu)以及一位法语教师——多伊娜·科尔尼亚(Doina Cornea)。因此,罗马尼亚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其他更引人注目的例子,例如哈维尔从被监禁的剧作家到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非凡转变。
我首先讨论“意识形态”(ideology),因为在讨论下面要讲到的其他术语时,需要对“意识形态”有一定理解。任何把“意识形态”放在书名里的作者都在自找麻烦。我这样做部分原因是,如果书名里包含“话语”(discourse)这个词,本书的一些潜在读者甚至都不愿意翻开它。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话语”可能更符合我的目的(它并不让定义简化)。与这两个术语偶尔纠缠在一起的其他术语还包括“意识”(consciousness)、“合法化”(legitimation)和“霸权”(hegemony)。我将如何理解这些术语,看它们在这本书中扮演什么角色?
最容易阐述的是“意识”,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我分析的兴趣范围。意识自然是任何涉及民族价值观的社会经验要素之一。一种民族意识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有趣的问题。但这并不是我要讨论的问题,只是间接地涉及(我讨论的人类行为隐含着某种形式的意识)。如上所述,我对正在形成和通过精英话语复制的民族意识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大众”意识也不太感兴趣,因为大部分的行动发生在知识分子和党内官僚之间,这些行动对广泛的公众几乎无关。
我更关注表征(representation)问题,而不是意识问题。罗马尼亚的民族认同是如何被表征的,哪些国家意象被提出、被争论?我们该如何理解产生这些意象的社会空间?鉴于我使用的文献来源,这些意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话语性的,出现在与政治相关的公共话语中。
我使用的“话语”一词并非严格遵循福柯的用法(独立于作为话语主体的人),但我与福柯一样认为话语不一定关乎“意识”。此外,也像他一样,我认为话语除了承载它的言辞之外,还获得了自身的特性和自主性。具体而言,罗马尼亚知识分子涉足话语领域时会限制他们的行动能力,在这些领域里没有人能真正控制所说的话。当人们的话语进入一个话语领域时,它们就会立即可以被重新阐释,可以被抓住并用来反驳说话者本人。
按照这种理解,“意识形态”塑造意识的程度在于它通过社会关系中的经验和行动来发挥作用,而不是通过思考或听说这些关系来发挥作用。与其探究意识形态是否“反映”社会和经济关系,不如视其为贯彻和挑战这些关系的一种手段。
意识形态过程是一种斗争过程,不同的世界观在此发生冲突,它们相遇,并进一步促进人们接受或反抗现存的支配秩序。当我谈论民族意识形态时,我指话语层面的斗争,其中,“民族”或“罗马尼亚人民”的概念成为核心,有时会与其他类型的话语斗争(例如,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或国家)发生交集,这些斗争不在本书讨论范围内。(我并不认为民族意识形态等同于“民族主义”,这个词在本书中很少出现,因为它对一些东欧人来说具有负面含义,这是我想避免的。)
意识形态过程是支配模式中最基本的过程之一,正是通过这些过程,葛兰西(Gramsci)所说的霸权形成了。同意(consent)被铭刻于各种形式的胁迫(cohesion)之中,使服从的群体接受自身的服从地位。霍尔(Stuart Hall)很好地表达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意识形态为社会结构提供了“黏合剂”,并不是因为统治阶级能够细致地规定和禁止下层阶级思想层面的内容(他们自己也“生活”在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中),而是因为他们努力并且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将所有关于现实的冲突定义纳入他们的框架之内,使所有替代方案都纳入他们的思想视野。葛兰西明确指出,意识形态霸权必须通过现有意识形态来获胜和维持,并且它在任何时候都意味着一个复杂的领域。
霸权意味着话语生产和实践在全社会范围内的规范化,这种规范化极少引起被征服者的质疑。霸权是暂时的,只是一个程度问题,并非在所有社会的任何时候都存在。
然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完全缺乏这些意识形态过程。为了讨论这些案例,我更倾向于一种有些独特的用法——使用范围更窄的“合法性”概念。按照韦伯(Max Weber)的表述,这个概念并不意味着社会中的所有主要群体都接受该支配体系。它仅仅意味着部分人口的同意,剩下的人则没有坚持某种替代性的社会秩序。
合法性并不一定是力量的对立面,因为如果一部分人认为政权拥有合法力量,他们可能因此无法组织起来反抗它,这使得它“合法”。科里根(Corrigan)和塞尔(Sayer)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将人们)融入到政体中,让下层阶级哑口无言——让他们说不出话来,而不是积极寻求同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意义上的合法性可能与布尔迪厄(Bourdieu)的“支配性观念”概念交织在一起,那是被视为理所当然、无需言明且因此不会受到质疑的东西。然而,这与同意却有很大不同。因此,我们应该谨慎地假设同意是合法化的必要条件。
我认为,与葛兰西的霸权一样,合法性始终处于“过程”之中,并且与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斗争息息相关。在这两个过程中,辩论都特别重要,它通过掩盖辩论发生的前提来构建霸权或合法化意识形态。辩论促进了某些基本前提的一致性,我们就可以将其视为“合法化结果”或“合法化时刻”。辩论在产生此类结果方面的重要性表明,意识形态领域主要是非同意领域,而不是意识上、自愿的信仰领域。
因此,理解合法化过程及其所涉及的更广泛的意识形态运作机制的基础,是将语言视为一个存在争议的领域,同时也是一个存在共识的领域。例如,在“民族”的存在等基础上达成共识。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多元、重叠、分散的话语空间,而不是相对统一的话语场,这一点因个案而异。在罗马尼亚的例子中,党的控制使话语场域比大多数情况下更加统一。
在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时期,如果说存在一种霸权的思想体系,那就是民族意识。几乎所有罗马尼亚人都接受民族意识的重要性,接受它所伴随的社会统一(及其隐含的内部社会矛盾的淡化)。据勒福(Lefort)分析,“极权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特征是构建一种统一的话语,明确宣称社会领域的同质性。这使民族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主义罗马尼亚的霸权。
然而,认同“民族”存在的罗马尼亚人对于如何定义和保护民族却众说纷纭。一些人认为,党试图垄断民族话语反而会使民族意识形态失去政权所谋求的认同基础。综上所述,我认为,罗马尼亚围绕“民族”的斗争是思想体系和合法性的角力,而非霸权的争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合法化和霸权并非一成不变的结果,而是持续不断的斗争过程。换句话说,斗争才是永恒的主题。
然而,这场斗争的过程不仅涉及个人和团体,还涉及话语本身。我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指出,1947年到1989年间是两种强势话语交锋的焦点——马克思主义和民族话语。“民族”概念带着数十年奠定的坚实基础进入这场斗争。在与马克思主义的交锋中,民族话语展现出将后者纳入麾下并颠覆其理论基础的能力。因此,“民族”是一个霸权符号,具有结构性特征。民族的话语能够打断其他话语(参见拉克劳的论述)并重新定义它们。强调统一和延续性的民族话语最终胜过了强调差异和变革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结果表明了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参与意识形态建构的另一个层面。
本书未使用人类学家中常见的专业语义来使用“文化”一词,尽管我对待研究主题的方式与当代人类学界重新思考“文化”的含义和意义息息相关。相反,在这里,这个词更接近于日常语境中的用法,尤其是“高雅文化”的含义——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和学者们创作的东西,有时面向相当狭窄的专业受众,有时面向更广泛的公众。我使用“文化政治”(politics of culture)这个表达来指代这类文化生产者群体内部以及他们与“正统”政治领域之间发生的冲突和运作过程,后者试图管理和塑造正在产生的文化。
文化政治研究通常沿着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中那句广为人知的话所开辟的道路前进:“人与人之间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争夺别人耳朵的战斗。” 我对罗马尼亚文化政治的探究关注政治和知识精英阶层不同派系之间通过话语展开的争夺,他们努力压制异议的声音,争取“耳朵”,这对于获得资源、让他们的声音被更广泛地听到至关重要。(文化政治也发生在除精英阶层之外的许多领域,例党选择性地鼓励或压制各种形式的流行文化。然而,这些形式不在我的讨论范围之内。)
并不是所有的人类语言都充满争论,并不是每一个说出的词都带有政治色彩。但在罗马尼亚(和其他高度集权的体制中),文化的政治化使争论变得无处不在。这影响了文化作品的创作方和文本解读方式。我的研究关注文学批评、历史、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政治化文化作品,探讨我们如何阅读其中的一些文本。
文化政治存在于所有类型的社会之中,作家和学者们不断塑造和修订着定义各自领域的经典作品,比如树立或毁坏乔治·奥威尔的声誉。然而,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制度的学者而言,文化政治尤其引人关注,他们分析的主要政治形式通常是知识分子和党之间的关系。
大量关于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语料来自流亡艺术家和学者,他们拥有作家与审查者、历史学家与党之间斗争的亲身经历。事实上,流亡者一直是此类详细信息的最佳来源,尽管他们令人不快的个人经历往往使他们的叙述带有被围困的知识分子捍卫真理和艺术免遭权力侵害的英雄故事色彩。这些著作大多详细描述了学术或其他领域(例如历史或文学)与“党”的关系,后者通常被描绘成一体的存在。研究过程包括清洗或恢复某个作家或思想家的名誉、审查制度的“博弈”、出于政治动机的研究主题或小说主题的转变等等。最好的研究既区分了生产者群体内部(不同类型的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差异,也区分了官僚机构内部(例如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差异,承认政治进程比领导人简单操纵的文化生产更加复杂。
为了阐明本研究与其他同类研究的区别,我将简要比较我与一些代表作的方法。比如,南希·希尔(Nancy Heer)研究苏联政治史的著作。尽管年代久远,但在概念上比许多近期作品都更精巧。该著作令人钦佩地拒绝了党和学者之间简单的二元对立,并且没有将后者视为党手中的被动工具。希尔强调双方互动和党内政治的复杂性,这会产生相互矛盾的信息,并促进史学界内部的斗争。她还将史学方法视为一种积极的力量,而不仅仅是任性权力可以随意揉捏的工具。
然而,希尔的论述没有深入探讨学者面临的利害关系。此外,她倾向于将“学者”视为故事中的“好人”,却没有充分解释这种评价应该基于哪些社会或道德准则。她似乎认为捍卫“真理”或“科学”规范的人就是在做正确的事。相比之下,我并不认为捍卫“真理”是理所当然的事。我试图比希尔更详细地展示捍卫“真理”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诉求,以及这种诉求揭示了哪些社会地位和斗争利害关系。我研究的群体并不是基于对“科学”或“真理”作为价值观的盲目服从。
什拉彭托赫(Vladimir Shlapentokh)对苏联社会政治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偏向,太偏爱“专业主义”和“学术价值观”(这些概念本身并没有经过审视)。尽管如此,他的著作在对斗争领域的社会学研究方面要比希尔的著作更加精细。例如,他对学科定义以及社会学从哲学中诞生的论述尤其具有启发性。然而,虽然什拉彭托赫提到社会学的发展表明了社会主义环境产生的影响,但他并没有解释计划经济体制如何为文化生产创造出一种特殊的环境。
同样的概念缺失也出现在另一项杰出研究中。1975年,加博尼(Gabanyi)详细考察罗马尼亚作家与党之间关系。相比于希尔和什拉彭托赫,加博尼对参与者的诉求持相对中立的态度,并且和他们一样,她细致地呈现了一个复杂的文化政治互动领域。然而,她也没有明确说明社会主义环境的性质或正在发生的斗争性质。
我的分析与这些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我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动态及其对文化生产影响的模型。我的研究形式上与卡加利茨基(Kagarlitsky)的研究最为接近,他也对知识分子活动领域进行理论化,尽管他使用的社会主义模型与我的略有不同。沙菲尔(Shafir)的概念虽然没有那么全面,使用的术语也与我不同,但更接近我的模型。因此,本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罗马尼亚置于明确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型和对知识分子活动的明确理解之内,其他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文化政治的论述则没有做到这一点。我希望这将有助于进一步的学术分析,这些分析有助于完善我仍然粗糙的概念,或提出更好的模型。
【可打赏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