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淀和硅谷,有候鸟老人的家么?
作者 | 冉冉
小乐写在前面: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我的朋友冉冉,一位环境政治学者。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是“一个飘荡于北京海淀黄庄与美国加州硅谷之间的跨文化育儿实践者。一个间歇性“焦虑”,需要依赖社会科学的想象力来排解日常养娃的鸡飞狗跳和自我治愈的妈妈。”
因为同样研究环境社会学,环境政治学而认识,又同时在湾区生活,虽然一北一南距离甚远,但我们依然会隔三差五举家开车吃饭聊天。当前一阵子聊起湾区华人家庭的养娃状态和社会阶级,种族等各方面因素之间的关系时,我们说起了蓝佩嘉教授的研究,于是便有了这篇约稿。谢谢冉冉。
01
跨国带娃受挫的焦虑:自找苦吃与鄙视链
在一个“贸易战”与中美“脱钩论”大行其道的日子里,我“抛夫弃女”从旧金山独自飞回北京工作。飞机上,我忍不住因与他俩的跨国分离而偷偷抹眼泪。“阿姨别伤心了”,一个温柔的声音传到我耳边。我抬起头,下意识地用衣袖蹭蹭鼻涕,试图掩饰自己的困窘。然后发现,我不是那个被安慰的“阿姨”,难道飞机上不只我一个人在哭泣?
空姐正在安慰的是坐在前排的另一位伤心“阿姨”。“连续飞两个来回,也没休息,这次进不去,下次试试从夏威夷走,那边好很多,这(加州)太严了。” 原来,这位奶奶是不远万里去硅谷带孙子的,没想到在机场被拒绝入境了,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出入美国太过频繁。。。
阿姨是个“候鸟式”的越洋带娃老人。为了带孙子,她舍弃了自己在国内跳着广场舞的安逸退休生活,频繁往返于太平洋两岸。但因签证的限制,老人们只能每半年轮岗,于是产生了“候鸟式越洋带娃老人”的说法。更麻烦的是,候鸟老人跨国带娃的努力屡屡受到美国机场海关人员的刁难。有硅谷“码工”们在分享各类闯关“小黑屋”攻略的同时,也发出了“有本事冲我来,别侮辱我爸妈”的不满和愤怒声音。

飞机上不约而同抹眼泪的那一刻,我与阿姨本应“同是天涯沦落人”– 我们的伤心都源自跨国异地带娃受挫所带来的焦虑。然而,阿姨与我却无法认同彼此的选择,甚至开始指责(judge)对方接受跨国带娃这个“命运”安排的正当性。
在阿姨看来,我应该赶快辞掉国内的工作,安心在美国带娃,全心全意支持老公在硅谷的事业发展。她问我,“你就这样撇下孩子老公自己回国工作,怎么放心?你老公又要上班,又要一个人带孩子,你就不心疼?”
我则在闲聊中质疑,“您儿子儿媳为啥不自己带娃呢?您这么大岁数来回跑多辛苦…他们回国可都是精英,这样您就不用再看洋鬼子脸色啦。”阿姨与我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推搡着、“成就着”,把对方的心理焦虑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为什么阿姨与我“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缘分非但没能形成对彼此伤心境遇的同情、理解与安慰,反而加深了彼此的焦虑?
小乐在之前《女性主义一路高歌,妈妈的憋屈无人可说》一文中专门系统介绍了英语世界的女性主义研究作品对于职场妈妈面临的各种社会结构性困境的讨论。文末,小乐敏锐的观察到,“忽视结构性的矛盾,把每一个她所经历的困境看成她的个人问题,于是无限细分出不同类型的妈妈,走上鄙视链的不归路。”
这句话让我突然脸红起来,脑子里盘旋的都是飞机上与那位阿姨同患难、共焦虑,但仍争分夺秒“鄙视”对方的场景。我看不惯那些指望老人带娃的年轻父母,也看不懂那些争先恐后帮着带娃的祖辈们。
表面上看,如果阿姨不帮着带孙子,就不会遭遇如此委屈。阿姨则批判了我的自私和不顾全大局。倘若我辞掉国内的工作,就能实现家庭的团聚,支持老公的事业。然而,我们都把对方的困境视为一种“自找苦吃”的个人问题。
02
发现结构:社会学想象力中的教养焦虑
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开篇就讲:“社会学家有责任向一般读者阐明,他们的私人困扰并不只是个人命运的问题,而是和整个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密不可分。”
现在,就让我们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去看看那些结构性、制度化的形塑力量。有别于亲职焦虑的心理学分析,社会学理论需要说明宏观抽象的社会不平等是如何转化为微观的个体焦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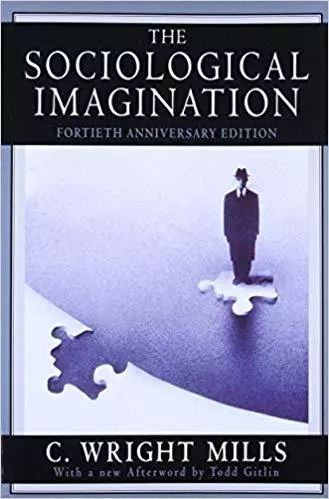
台湾大学蓝佩嘉教授的近十年来对台湾和美国华裔移民家庭的亲子养育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社会学家的思考与答案。她的两本新书,Raising Global Families: Parenting, Immigration, and Class in Taiwan and the US 和《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帮助读者将个人化的教养经验与亲职焦虑放进更大的历史、社会、阶级、族群、移民与全球化的脉络中来思考,体察我们的焦虑与困顿其实不单纯是个人的挫败与限制,而是其背后结构性的文化与制度困境。
蓝教授对美国华人移民家庭的研究展示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移民家长如何根据美国的社会教养制度来动员跨国资源,协商建构文化差异下的亲职身份。但是,这些“安全策略”不但经常造成非预期的效果,而且会强化父母的焦虑与不安全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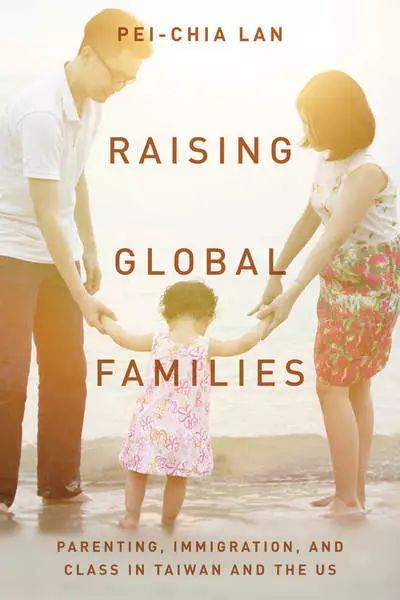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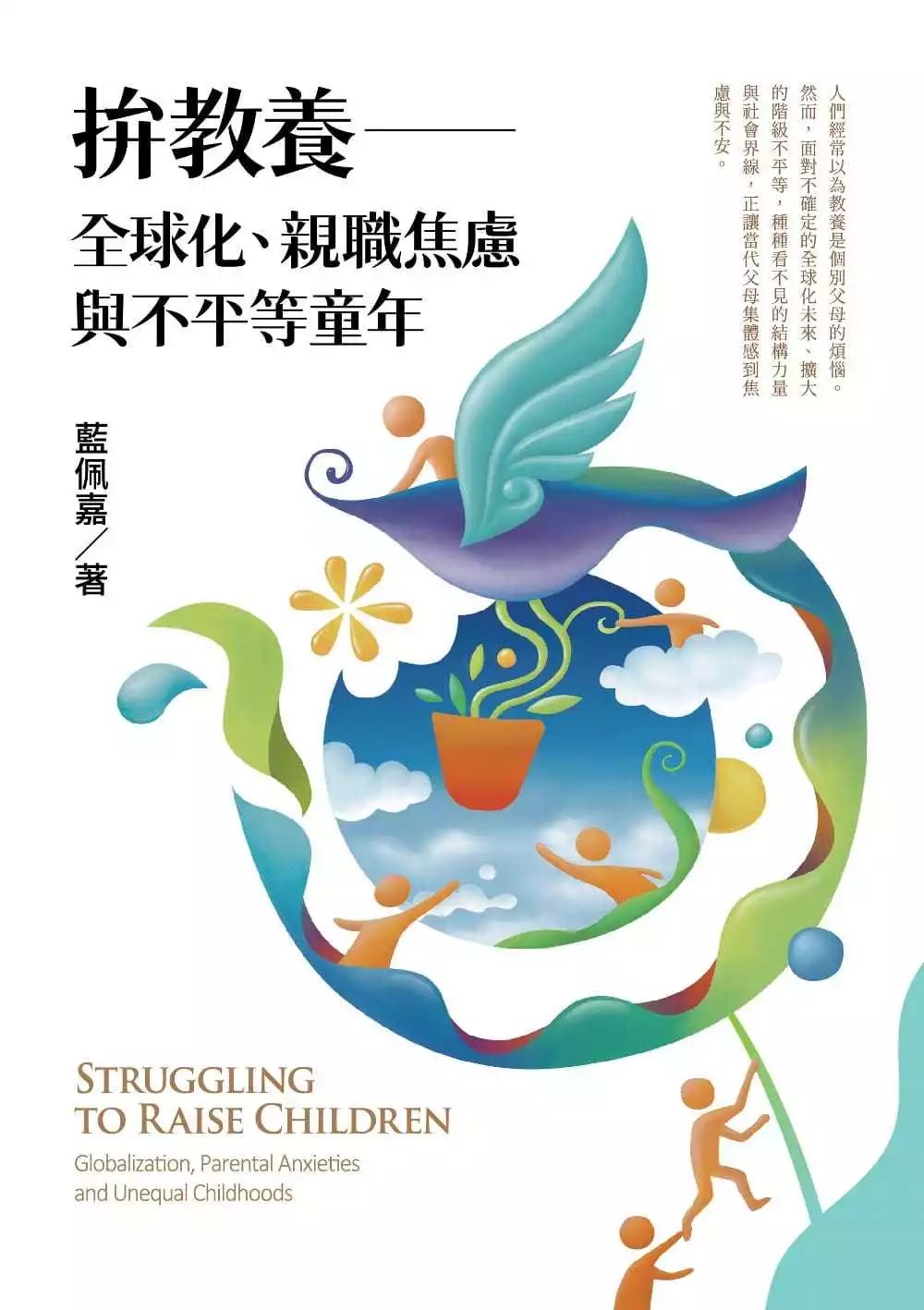
例如,书中展示了一个焦虑的蓝领工人阶层移民父母的日常,大致故事线索是这样的:父母阶层下降来美打零工,但是,孩子越来越美式,自由散漫“不听话”。爸妈想辅导孩子写作业,孩子却说爸妈水平不够,连英文都讲不利落。孩子觉得父母去学校让自己在同学老师那里丢人现眼,父母感到失去了权威,想打孩子教训一顿。结果,孩子威胁父母要报警,父母则威胁孩子报警之后会被送到黑人家庭寄养。同时,父母也不得不担心因为打孩子被政府知道而失去理疗保险等低收入家庭的福利。
与工人阶层的移民不同,人们以为工程师在美国的工作环境相对容易平衡家庭和事业,社会环境也鼓励爸爸带娃,让娃妈过上“守寡式育儿”生活的概率不高。但是,蓝佩嘉教授却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工程师爸爸们在美努力带娃推娃,可能是在制度化种族主义(institutionalized racism)的职场中遭遇了“亚裔天花板”的束缚而转移注意力,甚至把希望都寄托在让孩子实现阶层跨越上的一种表现。
那些躺枪的爸爸们,这不是你们的错,你们也是结构中的受害者。人们通常认为第一代移民很可怜,为了孩子的教育,宁愿忍受自己在异国他乡的“阶层下降”。这通常被视为一种为了后代而做出的“牺牲”。
同时,蓝教授在书中也描述了亚裔孩子的成长烦恼。他们是在父母的这种“自我牺牲”的阴影下被推大的。很多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不断强化自己的牺牲与隐忍,以换取孩子的奋斗和优秀甚至愧疚感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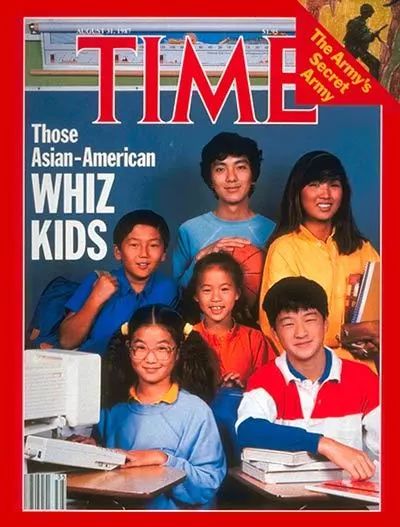
图为1987年时代杂志封面,亚裔孩子的刻板影响由来已久啊。
此外,来自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文化刻板印象为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提供了心理基础。如果你学习好,人家会说因为是你亚裔啊,天生应该学习好。如果你学习不好,人家会说,有没有搞错,你是亚裔,你应该天生很聪明啊!
如果你运动好,人家就会像对林书豪一样说,你不该出现在篮球场上,快回中国吧,打乒乓球,弹钢琴才是你的特长。如果你运动不好,人家会说,他就是亚裔的书呆子男。
如果你不会中文,人家会觉得你的脸和你的英语不搭,你是中国来的。怎么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如果你完好保存了母国文化,午饭带了正宗的三鲜馅饺子,人家就会嘲笑你盒饭的滑稽味道,导致你饿肚子回家,下次让老妈给你按照“Panda Express”的菜谱带饭…

图为美式中餐经典名菜Orange chicken
蓝教授的研究没有直接触及“候鸟式”越洋带娃老人的话题,但受其研究思路的启发,我接下来将这些老人的困境放在全球化科技劳工跨国流动的结构性视角上来考察,尝试回答为什么说这是个社会结构性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的自找苦吃。
事实上,“候鸟式“越洋带娃老人的困境的背后,正是全球化背景下跨国流动的中产科技移民经历的结构性脆弱。
P.S. 读到这,细心的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你只分析阿姨,不用这套理论也给自己照照镜子呢?嗯,考虑到我自己在跨国母职中面临的焦虑罄竹难书,就不在这篇里和阿姨一起比惨了。相信有一天终能将跨国当妈的焦虑化为码字的动力,另立Flag专门讨论。
03
越洋带娃老人与硅谷科技移民的结构性脆弱
大量来自中国的物美价廉的“码工”是成就硅谷科技神话的劳动力基础。(注:我用“码工”这个称呼代替工程师完全没有贬低的意思,而是希望沿用有趣的网络习惯用语。我家娃爸也是码工,我是码工家属)。
这些华人码工“话少活好”,低调恭顺。他们主动加班到7点,然后享用一顿符合亚洲口味的免费晚餐,在满足思乡味觉的同时,对老板心怀感激。他们不那么热衷于“老婆孩子热炕头”,周末去公司加班也可以成为少带娃的正当理由。
这些勤劳、聪明、克制隐忍的特质让老中码工们成功获得其职业身份,成为科技巨头HR眼中的理想雇佣对象。他们在为公司卖命的同时,也换回了至少六位数的年薪,股票期权和追求“美国梦”的权利。

网剧YAPPIE把亚裔工程师的生活描绘的活灵活现
听上去,这是一桩岁月静好的交易。但背后,是谁在负重前行呢?“一个HOUSE、两个娃、一只狗”的美国梦对于老中“码工”是仅靠个人的勤劳、勇敢与智慧实现的么?
现实是,他们的背后通常站着两个招之即来的国内大家庭的鼎力支持。人们会问,六位数的年薪还支撑不起这样的“美国梦”?我们通常看到的是,一个码工在用六位数年薪支撑一家老小的运转。却很少反过来提问:是怎样的家庭支持系统,在支撑一个“码工”获得并维系这六位数年薪呢?
“候鸟式”越洋带娃老人就是维系这个美国梦背后的家庭支撑力量。美国梦的家庭版本首先要求个人脱单,进入有娃的核心家庭生活。在异国他乡,从结婚买房开始,到生娃养娃,每一步都需要获得远在母国的两个大家庭的全方位资源支持。
宇宙中心的房价、昂贵而稀缺的幼儿园、外包家务劳动中的经济和文化成本, 这些看似属于个人消费范畴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砸钱就能搞定的。跨国输送的不只是人民币兑美元的额度,更多的是隐形的,来自父母甚至亲戚的“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带娃、遛狗、做家务、种院子…
虽然看上去只是帮孩子带娃做家务,但这些琐碎的大多足不出户的劳动却让儿女成为了雇佣关系中更符合雇主期待的员工。而这些老人,其实也成为了资本主义科技产业人才阵营中隐形的劳动力。
阿姨的儿子儿媳就职于令人羡慕的硅谷FLAG “大厂”,是分别拿着六位数年薪的双码工。小两口难以在维持高强度工作状态的同时独自承担密集的带娃劳动,请老人帮忙成为一项必须。

图为传说中的FLAG
倘若没有候鸟老人一次次艰难跨越重洋,老中码工们将难以加倍努力投入职场。他们将不得不为娃生病而请假,为接送娃而减少加班,为让娃吃口热的而拒绝出差,为娃哄睡而中断夜间视频会议,在娃夜里哭闹的第二天早上去公司猛灌咖啡续命。
这些都是那些号称强烈支持家庭价值观的大厂老板们不那么喜闻乐见的状况。没错,这可以算得上那些立着“don’t be evil”牌坊的老板们的伪善。
然而,这些候鸟老人在进入美国,努力为这个社会的科技劳动力提供无偿密集家务服务的时候,却屡屡遭遇美国社会包括签证、医疗、福利等诸多方面的制度性排斥和种族刻板印象的歧视。
更糟糕的是,这些结构性问题通常会在全球化的逆流,中美关系的脱钩,政治领导人的疯狂时刻露出异常狰狞的面目,成为个人难以逾越的一道墙。
2017年,川普刚上台不久,一位海关人员就傲慢地教训我: “川普的美国可不是你们这些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时代不同了。” 我一直把这话当作一句荒唐疯话。直到2019年,阿姨告诉我,她用尽浑身解数,也没能在旧金山机场走出那道玻璃门,抱着小孙子一起“回家”。
也许, 这套结构性的安排是让阿姨来美国做客,而不是回家的。当她自觉不自觉把美国视为家的时候,就引起了那些把自己建构为这个国家主人的结构制度的警惕和恐惧,拒绝和排斥。
04
忽视结构性力量的你、我、他
阿姨不关心国际政治和中美关系,不在乎谁当选美国总统,实行怎样的移民政策,她的儿子还有可能是硅谷华人工程师的众多“川粉”之一。她只是害怕在机场海关“小黑屋”被美国海关百般刁难与拒绝时的无助,不明白为什么这些高傲的“白男”不同情一位白发苍苍的奶奶跨国帮忙带孙子的急切心情,却把她视为有潜在移民倾向的“危险份子”。
自小就习惯了作为一个村,一所学校,甚至一个省的骄傲的老中码工学霸们,在说出那句“有本事冲我来,别侮辱我爸妈”的时候,表达了难得一见的不满和抗争,但也暴露了他们面临的结构性脆弱。
然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或者不愿承认,自己作为美国社会的一代移民,这种脆弱性不是因为自己不够优秀、不够努力,而是受困于以权力为基础的制度和结构性不平等之中。
阿姨和广大码工们都只看到了个人而忽视了结构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全球化、跨国流动、移民的结构性脆弱,这些概念似乎太不接地气。哪怕我研究的是政治学,也没有将这些时常挂在嘴边的学术词汇融入到带娃的经历中。所以,当读到蓝佩嘉的书时,我满心惭愧。
自从当妈之后,我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有的家长不自己带娃,甚至不能同情那些“留守儿童”的妈妈。
原来,我是被那些大力倡导“亲密育儿”、“合作培养”、“无条件养育”等以美国白人中产阶级为标杆的主流育儿叙事给洗脑了。将美式的“直升机式父母”甚至“铲雪机式父母”作为了教养标准,并以此来定义和鄙视那些不合标准的“熊父母”。

但我完全忽略了此类“标配”是在全球化竞争的大背景下,基于特定阶级、种族、社会环境和国家政策的一种特权式建构。其背后存在的结构性困境是社会、政治和经济权力分配不平等的体现。
有朋友反问,同样在硅谷科技公司打拼,人家土住老美、印度或俄罗斯码工为啥可以自己搞定带娃。为啥偏偏是华人需要父母远渡重洋?这是个复杂的好问题。其实这些不同的种族群体在养娃过程中受到的结构限制差别很大。
首先,不同族裔的文化,语言背景不同,哪怕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所面对的环境的复杂性和自己的适应难度并不一样。
其次,很多其他国家的移民,比如印度人,父母及其大家庭的足迹遍布硅谷的各个角落,从公园到图书馆。
第三,本地人自然有更丰富或灵活的资源来辅助他们养娃,比如有和他们住在“一碗汤”的美好距离之内的退休父母,有亲戚朋友推荐的可以信赖的临时保姆。

第四,对于没有老人帮忙的家庭,这里的家庭中也会有负重前行的妈妈在放弃或者搁浅自己的职业生涯。
对于生活在湾区的华人来说,我们较少找保姆带孩子,让妈妈全职在家即存在经济上的风险,又存在与母国文化上的冲突。而中国老人带娃通常是一种家庭养老的代际互换模式—- “我帮你带娃,你帮我养老”,其根本制度原因是社会养老保险体系的不健全。
以上这些因素,每一个都涉及到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的因素。而第一代华人移民之所以特别辛苦,也是因为要面临双重的结构压力,一方面是来自移民国家的阶级、种族、社区、职场、移民政策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母国的文化、性别、社会家庭政策等层面的钳制。
05
结语:看见结构,以同理心回应
蓝教授在书的最后用温情的语言提出了对读者的希望,她“希望透过诉说故事、分享经验,让我们多一点同理心来观察不同家长位置的差异,也提醒自己放下一些‘标准童年’、‘理想亲职’的包袱,成为怡然、放松的父母。希望读者能产生同理心而非同情心。不是同情不幸、可怜弱势,而是能够透过分析与比较,看穿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的作用,进而反思自身的经验。”
如果我能早点读到她的书,我应该不会去问阿姨“您儿子儿媳为啥不自己带娃?”,但会批判川普的移民政策、海关人员的种族官僚主义,疯狂的中美“脱钩论”叫嚣者和伪善的科技公司资本家。因为他们才是那些编织将普通人套牢的牢笼的人。
我也不想再问阿姨“您儿子为啥不回国”这样匮乏社会学想象力的问题。她老人家遇到的结构性障碍,不是儿子出国造成的错,除非他一辈子故土难离,呆在永远的家乡县城。
“候鸟式”越洋带娃老人的困境其实只是国内为支持儿女事业,背井离乡来到大城市照顾第三代的“老漂族”的海外强化版。

西二旗的“996”,深圳的 “251”,“5+2,白加黑”的基层公务员,他们的背后都背负着父母被连根拔起的“老家”。“老漂族”想象中的那个“远方的家”,无论坐标遍布北上广深,还是美国东西海岸,都人为设置了由结构和社会不平等筑起的有形无与形的墙,让“老漂”们对家的想象成为一种迷思和焦虑。
尽管我们无力推翻这堵墙,并且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其“结构”的一部分。但能做的是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不为 “结构”添砖加瓦,不参与到鄙视链和焦虑制造中去,温柔的对待自己和她人。
-推荐阅读-
– 版权声明 –
文章版权归成长合作社所有 欢迎转发朋友圈
转载方法请见下拉菜单
关注我们

